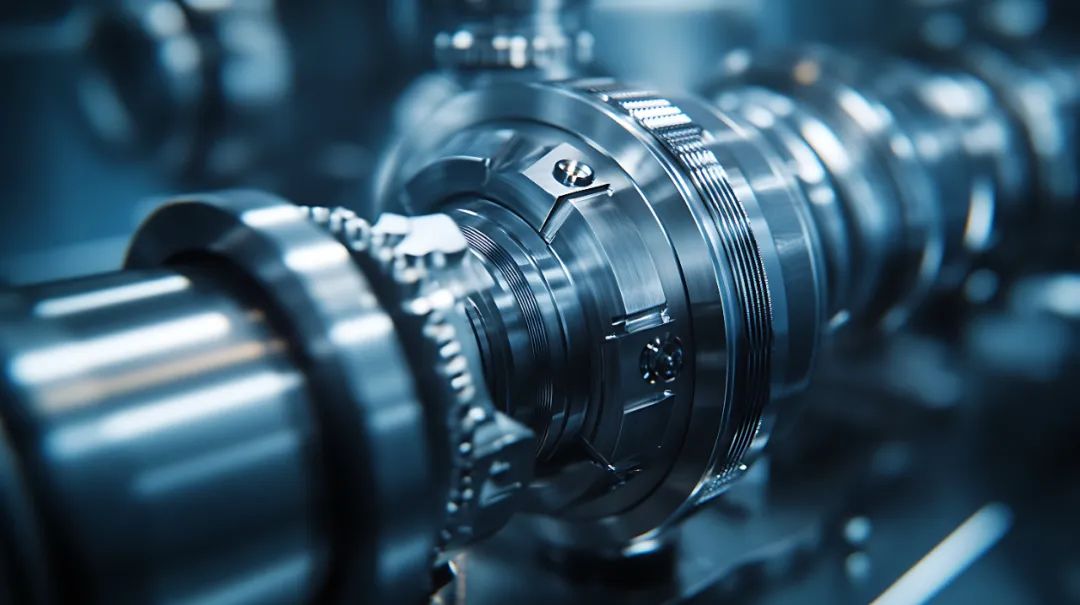和勇气一起生活
蓝蓝
哲学老师的推荐
“失去了天堂呵!”
塔列朗老头有一次说:谁要是没有在1789年生活过,那就压根不算生活过。和他同时代的成千上万人都持有这种看法。
这是侯焕闳先生翻译的《西方风俗史》的开头几句话。拿来放在这篇文章的前面,则是因为我觉得,如果要是没有在上世纪80年代经历过疯狂买书、读书的日子,便和塔列朗老头的感觉一样,也失去了享受阅读的天堂。
1986年,我在深圳粤海湾边的大学读书,教我们西方哲学课的老师名叫刘小枫。他中等个头,戴副眼镜,圆脸微胖,神色肃穆,几乎从没有见他笑过。
西方哲学课是大课,每次走进阶梯教室,座位都会被先到的男女学生们用书包、课本、眼镜盒等等占据了。那个时候的深圳大学还在初建阶段,多邀北大、清华等学府的老师客座授课,也有诸如刘小枫、王晓明这样日后声名日隆的年轻老师。刘小枫老师在学生中名气很大,因此,虽然有很多人根本听不懂他讲的内容,教室里也经常是济济一堂,连门口都站满了人。
因为上大学前就开始写诗,所以听到他讲海德格尔及其对荷尔德林的研究时,就特别用心。做笔记就不说了,下了课会向他继续讨问。于是,我的书包里便有了几叠复印的海德格尔的文章,以及荷尔德林的诗歌。
“好好读书。”他面无表情地说。
“要学好外语。外语很重要。”他又说。
说话那会儿,我即将离开深圳大学,到郑州大学继续学业。遗憾的是,我读过不少书,但对外语的学习却辜负了他的期望。到了1988年初,刘小枫老师来信询问郑州是否有卖《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我恰好刚买到这本书,便寄给他,顺便在信中讲了自己回到河南后的苦恼和压抑。很快,我接到他的回信,他向我推荐了保罗·蒂利希的《存在的勇气》—“读一读这本书,或许对你会有帮助。”他写道。
谁知道,多年后我竟会为此写下了一篇文章。
盯视着那根针头儿
这是一本只有一百多页的薄薄的小书,绿色封面,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出版,印数只有5000册。那年春天,我在郑州农业路口的三联书店买到它时,定价只有1.5元。
保罗·蒂利希是谁,在读到《存在的勇气》之前,我一无所知。自然,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深奥的神学哲学也不是我那肤浅的理解力所能够掌握得了的。好在有读书积累下一点存在主义哲学的基础知识,在阅读这本《存在的勇气》时,也渐渐了解了这位曾作过军中牧师的哲学家对于“勇气”的看法。显然,我读这本书的初衷是想解决我自己遇到的具体而世俗的问题,但这本书却把我领到更深的思考和更为广阔的精神领域中。
1952年,保罗·蒂利希在耶鲁大学作了一系列演讲,他选择了“一个集神学问题、社会学问题和哲学问题于一身的概念即‘勇气’来做题目”。他认为,“少有能像‘勇气’这一概念那样有助于人类处境的分析”。他指出,“勇气”一词并不是著名的里克阿斯将军关于“什么是可怕与什么可以大胆地去做”的知识和定义,同样,从苏格拉底也承认“我们到底未能发现什么是勇气”这一结论来说,此种“失败”在苏格拉底的思想体系里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蒂利希希望人们知道,要想理解什么是勇气,必须首先要有“对人和他的世界、他的结构和价值”的理解。因此,探讨“勇气”这个属于伦理学的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存在的性质”这个本体论问题。—这便是《存在的勇气》这本书结成集子的最早缘由。
以当年刚刚20岁的经验和学识,我几乎是半懂不懂地翻完了这本书。最大的收获是,我终于知道焦虑和恐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没有具体对象的,后者却有一个真实的对象。
“勇气通常被描绘为心灵克服恐惧的力量。”
“焦虑是从存在的角度对非存在的认识。”
“焦虑力图成为恐惧,因为恐惧能为勇气所遭遇。”
上述这几段话,都是22年前被我用铅笔在书里行间画下的。不仅有这些条条道道的画痕,在书眉和页旁,还写有一些旁注,譬如对一些我不熟悉的哲学家、不熟悉的观点作的注释:斯多葛学派的主张和阿奎那的神学理念;塞尼加的哲学观点以及恩格斯对他大加贬低的评价(说他是尼禄宫廷中头号阴谋家);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等。在那个时期,我有许多读过的书和这本书的情形一样,书的空白处,几乎就是一个年轻的写诗人学习和思考的练习册,它虽显幼稚,但却认真。我曾抄录过书中涉及到的很多定义,我了解到焦虑的三种类型是什么,我知道了在保罗·蒂利希那里,“勇气”即对存在的赞美和保护,亦即“不顾非存在的威胁而对存在进行自我肯定的”努力。
对《存在的勇气》的初次阅读,教会我在遇到苦闷或者焦虑时,应该去找到那蒙在焦虑背后的影子,我知道,只要掀起它的“盖头”,我将不再惶恐。
某一天,我因发烧在医院输液,忽然注意到前面几位患者因为害怕那小小的针头,都扭过头不看护士打针的动作,随着一下龇牙咧嘴的痛苦表情,完成了注射。我则伸出胳膊,和以往一样,一动不动地盯视着针头刺进皮肤—呵,作为焦虑力图成为恐惧的佐证,我猛然意识到自己的这个习惯背后隐藏的潜意识。能够面对恐惧,这便是不再惧怕它的第一步。这是最世俗化意义上的一个例子。
自我与极权,以及勇气和上帝
在我所有的藏书中,有二十几本书是经常要读、反复去看的。很多年来,无论搬了多少次家,我不离不弃地带着它们。这些书大多被我翻看磨损得很厉害,书页上都是画的线道,写的字,甚至有随手写下的诗句。《存在的勇气》算是其中一本。
某年中秋,一位诗友因为情感的烦扰,找我倾吐。几番劝解后,我起身从书柜里找出《存在的勇气》递给她,似乎那是一本解除烦恼的生活指南。几天后诗友没有如约归还此书,我心中开始忐忑,直接找上门去,见其赫然放在案头,用镇纸压住半边,显然是主人正在翻看。我有些羞赧地要将书讨回,诗友“耍赖”说再买一本新的送给我,这本旧的她留下,理由是她太喜欢那些旁注和眉批,还有画的着重号、标志线。
此等隐私记录怎能落入他人之手?几乎是怀着失而复得的心情,回到家我重新打开这本书,从最后一页开始朝前翻看。对于一个从小就受到无神论教育的人来说,“上帝”这个词始终只是作为一个模糊的概念存在。在深圳大学读书时,我听说刘小枫老师是基督教徒,曾大为吃惊。在当时,我根本无法理解一个智慧的人会把自己交给“上帝”。我问他:你相信一个抽象的上帝还是相信一个具体的上帝?他平静地回答:“当然是一个具体的上帝。基督教最反对去信一个抽象的上帝。”
具体的上帝是什么样?我不知道。
蒂利希告诉我:“上帝来自它自身,是绝对自由。它的一切皆由它创造。”这番话是他在论及“作为自我存在的勇气”时谈到的。显然,他指的是当“作为部分而存在的勇气”成为人们加入到集体的伟大目标的选择后,虽则会令人感受到世界与人关系中的归属感和确定感,但它也会是各种极权主义和集体主义运动滋生的温床。此种选择并不是人们逃避空虚和无意义之焦虑的最好选择。而主张“自我存在的勇气”即存在主义的激进方式,自我将无限膨胀,直到隔绝和忽视了世界的参与。两种选择都隐藏着法西斯主义、极权集体主义互相转换的可能。蒂利希在读者感到茫然的时候,再次谈到上帝。在他提出的“绝对信仰”中,自我的个性化和世界的参与都将得到实现,但其前提是必须把“无意义”这一最可怕的焦虑纳入自身的存在。他指出,一切形式的存在的勇气“都在有神论的超越上帝的上帝的力量中得到重建”。这本将基督教新教和存在主义哲学杂糅在一起、谈论我们最缺乏的关于“勇气”的书,他以诗一般的语言作了结束:“存在的勇气植根于这样一个上帝之中:这个上帝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对怀疑的焦虑中,上帝已经消失了。”
保罗先生,你的基督果然并非是拿撒勒人耶稣的灵。因为在你的心中,耶稣身体里属人的灵完全被圣灵占有,而上帝就在那里。但是,你有句话震住了我:谈论存在就等于谈论上帝。
“神学家中的神学家”
记不清读过几遍《存在的勇气》。从一开始充满实用想法的阅读期望,到后来变成某种习惯,它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而我也在一次次惊奇地打量它。面对这本已经出版22年的书,它越来越年轻和陌生的面目令我惊讶。我常常翻开它,从随便哪一页开始读,似乎手里是一本我不曾看过的书。它的迷人之处在于看似宁静枯燥的阐述中深藏着隐秘的激情。由于它的引导,我又去读了更多神学和哲学书,翻阅过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蒂利希另一本《文化神学》。我对这位“神学家中的神学家”充满好奇—他极具洞见,行文严谨,有着可怕的辨析力。他对众多思想家和他们的主张了如指掌,其兴趣不仅仅囿于神学领域,他对历史、哲学、心理学和文学、艺术等都有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神学家的职责就是要把《圣经》的信息和当代的现实联系起来;他对其他宗教充满尊重和宽容;他对极权政治极其厌恶和警惕……
保罗·蒂利希(港台书译作“田立克”,据说是蒂利希自己在三个汉语译名中亲自选定,原因是作为汉字的这个名字笔画最简单)(1886—1965),原籍德国,一生中先后获得15个博士学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担任德军随军牧师,战后在几所大学讲授神学和哲学。1933年受法西斯迫害移居美国,曾先后任纽约神学院、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被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神学家,宗教哲学家,在学术思想界极具声誉。撇开他的专业神学哲学不说,在薄薄的《存在的勇气》一书中,仅关于文学和艺术就有相当精彩的论述。他谈论卡夫卡、加缪,谈论波德莱尔和兰波;他对浪漫主义各个时期的问题洞若观火。作为一个写诗的人,我居然在书中读到了这样一段可以用来阐释诗歌和描述诗人的话:“语言给人以从具体给定的东西中进行抽象的能力,并在作了这种抽象之后又返回到具体事物,对它进行解释并加以改变。最富有生命力的存在物,就是那拥有文字并靠此文字从被束缚于既定东西上解放出来的存在物。”
崭新又陈旧,有着一张未来面孔—22年前,刘小枫给我推荐了一本怎样的书啊!
《存在的勇气》
保罗·蒂利希 著
成穷/王作虹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
169页,15元
本网站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及音视频),除转载外,均为时代在线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协议授权,禁止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 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转载使用,请联系本网站丁先生:news@time-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