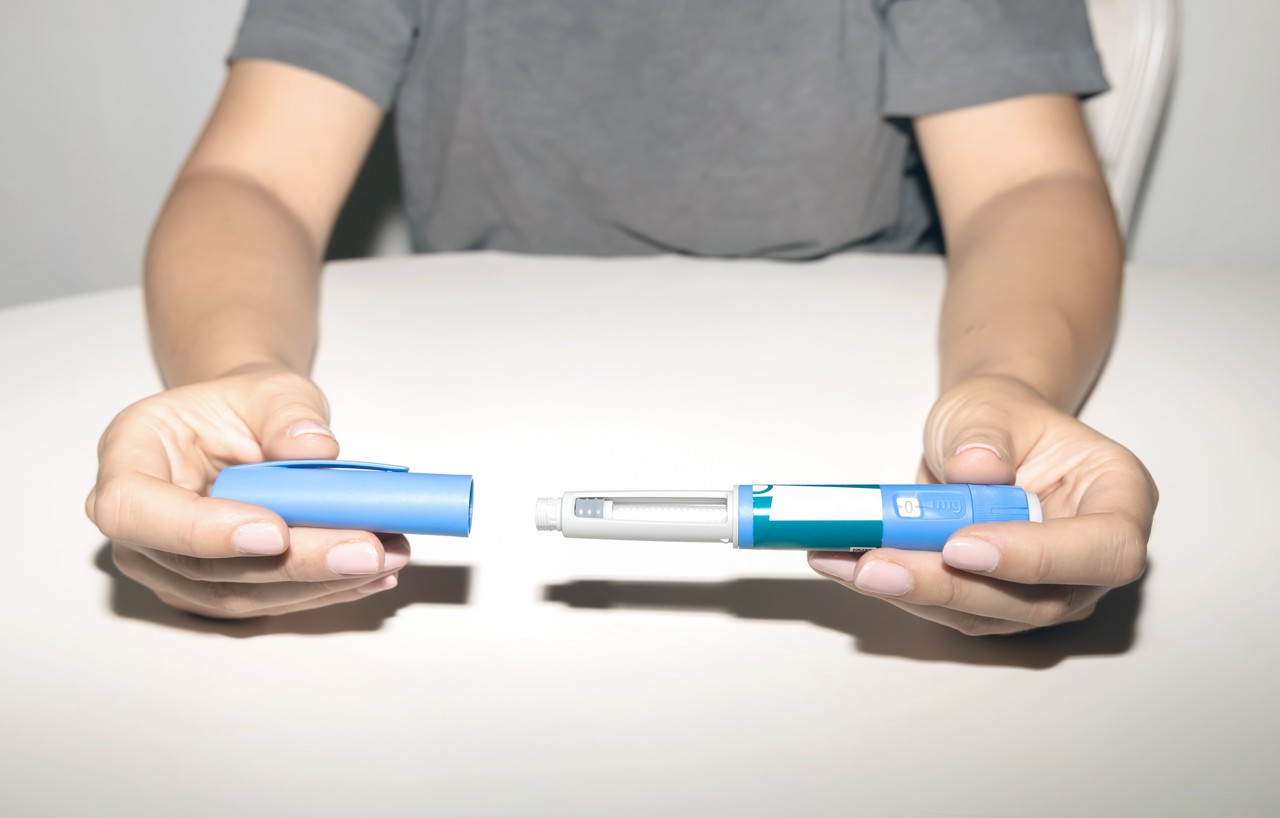后撒切尔时代,“左派”为何忧郁
“忧郁”(melancholia)最初出现于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及盖伦的著作,指的是人体四种体液之一的黑胆汁,据说,哲人、政治家和艺术家黑胆汁比普通人多,因此他们生性忧郁多虑。弗洛伊德运用精神分析,将“忧郁”带进“哀悼”的对立面,忧郁者对失落对象的眷恋不会减退,却持续存活,但忧郁也是哀悼出现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上溯“忧郁”的源头“失落”来看,又会发现原来“忧郁”不限于“精神分析”的范畴,而是关乎整个文化,而将“忧郁”从“精神分析”层面推向社会、文化甚至政治领域的思考,甚至从这些领域中发掘有关“忧郁”的新问题,正是本书作者们想要做的工作。
其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也不是着眼于个体的意识,而是社会与文化对个体意识的影响,他的许多病例都充满社会及文化意蕴,只是他发展出来的一套语言令人们感觉到学术的陌生感。然而不管这些专业语言对精神分析专业来说具备何种意义,它们早已借人们以充满歧义的语言,撒播于社会论述之中。《躁郁简史》的作者在文章里梳理出躁郁症怎样走入社会语言的过程。我们知道,精神分析在“忧郁”这现象背后发现在“躁狂”和“抑郁”这两极之间徘徊的精神病患,即躁郁症,然后透过被精神病学界公布的病例,躁郁症又进入了公众舆论。
“躁郁症”从学术语言走入中产阶级甚至普罗大众的讨论中,这标志着我们称为“忧郁”的精神病症,不再是个陌生他者,它现在就成为千百人自我认同的途径。因为在社会上有许多失败者、边缘人,他们一旦被称作“躁郁症患者”,就可以借着精神分析或精神病学家对他们的诠释,从而得到医治和拯救。爱密丽·马汀在《我现在宣布,你是个躁郁症患者》中引用维特根斯坦的话,也说明了一种行为背后总是为了实现渴望:就像亲吻照片中的人并不是认为那就是他,而是为了实现亲吻那人的渴望。而很多自称“躁郁症患者”的人向精神病医生求诊也有类似的目的,他们渴望被关怀,因为他们感到“失落”,这种“匮乏者”的“失落”恰好是个政治的问题。
如果你认为“忧郁”是个人的内在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中,为何那么多穷人都精神失常,或者那么多知识分子都是忧郁症患者?为什么压迫者和既得利益阶层永远从容不迫地生活?这也许说明了,不公平和充满压迫的社会,正是“忧郁”及其力量的泉源。从精神分析来看,“忧郁”本身具备了缅怀过去的依恋,但从文化理论来看,“忧郁”所依据的“集体记忆”,却是左派反抗的根据。既然弗洛伊德认为“忧郁”是“依恋”某种已经“失落”的人或事,那么某种属于过去的“快乐”,也可以引起充满政治意蕴的“忧郁”,而《快乐的回忆》与《反抗左派忧郁》两篇文章所讨论的问题,正好与此相关。
凯莉·汉弥尔顿在《快乐的回忆》开始处引用但丁《神曲·地狱篇》的话﹕“最巨大的悲伤,莫过于在悲惨中回想起快乐的时光。”与本雅明对“左派忧郁”的批判,同样从两个角度指向忧郁与快乐的特殊关系。在但丁的语境中,现在是悲惨的,而缅怀“失落”的“快乐”令人越发“忧郁”,本雅明的话则涉及他对“左派忧郁”的批判。本雅明目睹左翼知识分子在经历政治失败过后,沉湎于过去、理念和理想,以公义、反对不公平的事业而自豪,就像历史天使只顾过去被摧毁的世界碎片,而不顾进步的风暴。上世纪80年代,由于撒切尔主义以及各种被冠以新自由及新保守之名的政策得到胜利,令左翼知识界无从反击,更日益显出讨论“左派忧郁”的必要。
这左派并非狭义的左派。在今日国际社会中,各国政府实施更彻底的监控和立法,令各种激进的政治诉求变得软弱无力,许多已实现的平等权利议题又被重新压制,例如受压迫种族和同志平权运动,其中同志运动的理念,或多或少成为一种活在历史中的快乐回忆。在这保守势力回潮的政治时刻,对于左翼知识分子来说,“忧郁”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它令人重新思考应该如何“反抗”。
本网站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及音视频),除转载外,均为时代在线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协议授权,禁止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 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转载使用,请联系本网站丁先生:news@time-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