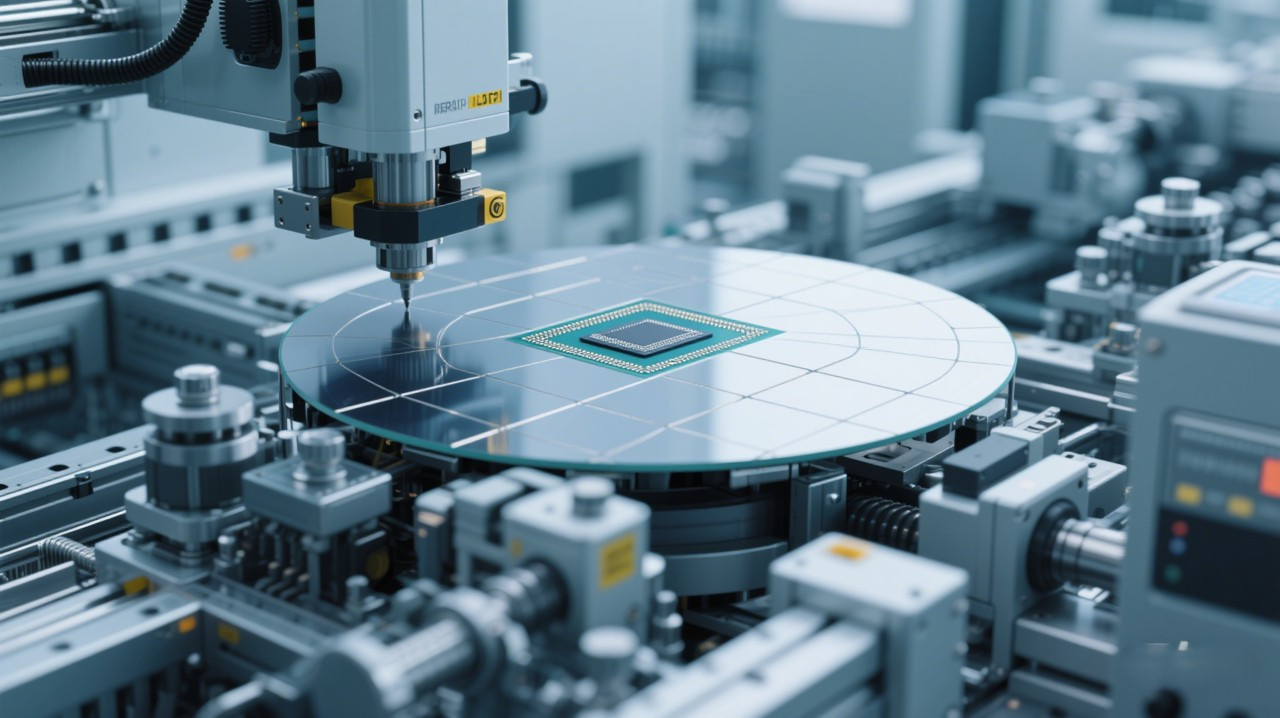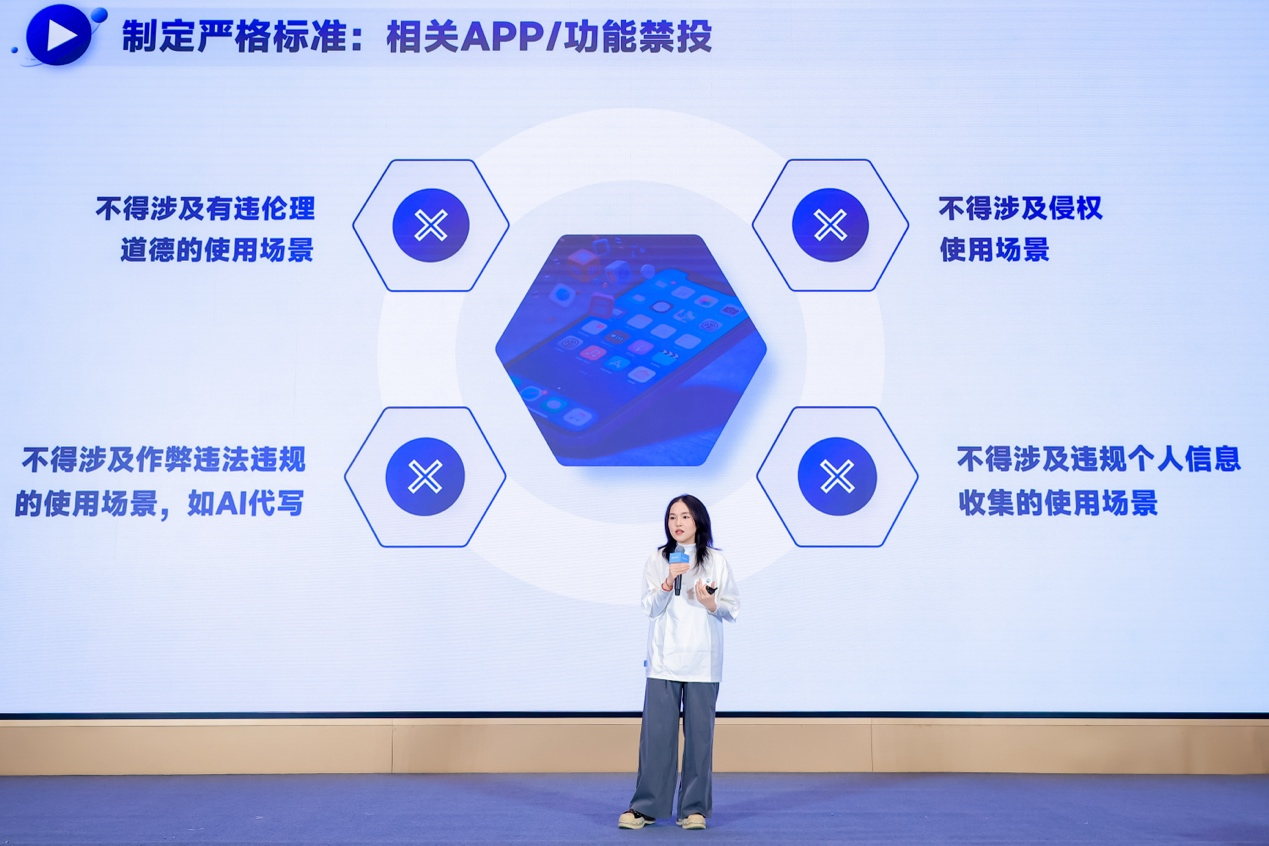刘小东画展《金城小子》 在现实的空间里写生
“这一次,我决定回家。”11月17日,刘小东最新个展《金城小子》开幕,在北京798艺术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厅里深灰的墙面上,他写下了这第一句话。
本报记者 喻盈 发自北京
1980年8月,17岁的刘小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在他走出北京站、去美术馆旁边的中央美院附中报到的路上,他一直为这座城市难以分辨的方向迷惑—因为在他此前的全部经验里,城市往往被铁路所贯穿,而一座城的中心应该在铁路的南侧—北京的布局,颠覆了他17年来由故乡金城所建立的“城市观”。
金城,辽宁省锦州附近一个围绕国营造纸厂而形成的小镇,工厂即是中心,工人及他们的家属构成人口的主体,四围是广袤的农村,工人与农民加在一起也不过几千人。
故乡在刘小东身心中留下的巨大投影,此后30年里似乎逐渐淡化。因为第一次的背井离乡,北京,就让这个小镇少年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学校的通知书上写着‘欢迎’两个字,现实却是很冷漠的,没人‘欢迎’你。生活里处处会碰到歧视,无形中就是在鞭策自己:你不是这儿的人,但你要变成这儿的人,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如今,他已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作品不断刷新中国当代艺术拍卖纪录的著名画家。毫无疑问,这座倨傲的城市早已不再怀疑他的归属,他变成了“这儿的人”,但他却发现,丢失了故乡。
“这一次,我决定回家。”11月17日,刘小东最新个展《金城小子》开幕,在北京798艺术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厅里深灰的墙面上,他写下了这第一句话。

图本报记者 郭杨 摄
近乡情怯
从6月底到10月底,刘小东在故乡金城画了4个月的画,一次经历东北的夏、秋、冬三季,这在他离家后的30年来是绝无仅有的。虽然作为一个重情谊、传统家庭观念深厚的东北人,30年来每逢春节他都要回金城,与儿时的朋友吃喝玩乐,但是每次停留的时间通常不超过一个礼拜。和大多数在外打拼的中国人一样,面对故乡,他心态复杂:“中国人都是这样的,混不好不敢回去,混得好也不敢回去,盘根错节的亲戚太多。”希望一切都不要变,希望父母永远不老,然而,谁也无法停止时间的脚步,无法预估城市化进程对过往记忆的超速蚕食。
所谓,近乡情更怯。
更多的顾虑,来自艺术的商业化。“我一直想回老家画些画,但总是越想越不敢回去,在父老乡亲面前画画真是件天大的害羞的事情。因为我也知道艺术品会成为商品,拿老朋友的脸去换钱,是很别扭的事。每次我想回去画都放弃了。这次正好赶上尤伦斯要做我的展,而且将展期提前了。这么短时间里我能做什么?回到家里,你能画很多东西,因为你熟悉。”
预定的展期,推动了这次返乡之旅。八个儿时的朋友,旭子、韩生子、肖老师、成子、郭强、力五、树军、小豆,成为刘小东画里的主角。他们中的大多数中学毕业后顶替父母的职位,进入金城造纸厂工作,如今有的提早退休,有的已经下岗。小豆是这些朋友里唯一的女性,身材样貌都姣好,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却已经退休在家;初中时教刘小东练习武术的肖老师,现在成了公安局的民警;一枪崩瞎了别人眼睛入狱的树军,如今开了个小饭馆,年近五十、喜得贵子;开KTV的郭强是小地方的“城里人”,走高端路线,在小世界大社会的历练中百毒不侵……选择描绘他们是偶然,“他们刚好在家”,某种程度上也是必然,“八个人基本概括了现在家乡人的生活状态”。
除了画画,大家在一起便是吃饭喝酒。酒桌上树军回忆起当年他在狱中经常收到刘小东的信,因为信封上“中央美术学院”的落款,使狱警对他很是刮目相看—但刘小东寄去监狱的书,却都被狱警扣下了。而郭强记得的往事是,小时候刘小东就曾拉住他画像,“那时候他就说我难画,因为我长得没啥特点”。
整日厮混,渐渐使刘小东心安:“最开始我很害羞,生怕打扰了他们的生活,也担心利用了他们。但通过画他们,这种顾虑被打消了,他们是那么的平常心,也不说画画干什么,也不讨论画的价格多少钱,不像城市里的人对这个这么感兴趣。他们喜欢和我在一起,无论我做什么他们都高兴,真的很难得几个月天天在一起。所以我的感受就是平常心太重要了。”
被淹没的工人阶级
如今的金城,工厂凋敝,老平房正在渐渐拆去,人们穿着滞后都会时尚十年的衣服,却也被城市化的进程裹挟,漫无目的地向前。
这当然远离刘小东的记忆。在他的少年时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厂宏伟高大,几十米的烟囱浓烟滚滚,汽笛声响,上下班的工人人潮汹涌”。与所有的东北工业城镇一样,金城经历了国营转制、工人下岗、圈地建房的全过程,“工厂被新建的楼房淹没,工人阶级被满街的后勤人员、买卖人淹没。我们忽然发现所有的城市都变成了一个样子”。
在画家返乡的日子里,造纸厂正处于停工状态。由于工人们发现工厂已经十年没有给他们交养老保险,退休保障都成了问题,忍无可忍,罢工抗议。刘小东画了一幅小画,记录下工人们闲在街上打牌度日的场景。“工人老大哥”式的骄傲早已消失殆尽,未来的茫然无着,使他们现在更羡慕农民:人家至少有地。为了活下去,有些工人会反过来去农村打工,帮助收粮食,做很多农活。“我发现他们的适应能力就像自然界的草,冬天来了,死了,春天来了,又活了。”刘小东在一幅速写旁以这样的文字描绘“发小”力五:“身体永远年轻矫健,头脑却像个老人,看见空地就想种粮食,看见粮食就想捡回家。有了力五,我们就不会忘记贫穷对一个人的心理和行为的长远影响。贫穷使人不会忘记最基本生活资源的重要和对失去它的恐慌。”
刘小东感到抒情的无力。在迅猛的现实面前,“我只能睁大眼去看,在有阳光的和没阳光的白天里去画他们,我能做的仅此而已,来不及抒情也来不及不抒情。”
他像电影导演一样精心挑选作画的场景。凝固的画面上有时间的痕迹与精准的叙事。他在旭子家徒四壁的狭小屋子里给他画像,桌上、地上的缸子、罐子,便几乎是全部家当;画小豆,选在台球厅,艳丽的短红裙,波浪形烫发,四十好几的小豆青春依旧,却被时代闲抛浪掷了韶华光阴;韩生子站在一片废墟里,单脚踏上坍塌的砖墙,“这里原来是商店,后来变成糕点厂,再后来是冰棍厂,后院有一个日伪时期的炮楼。近两年要开发房地产,把这里平了,因为离火车道太近,不让盖楼,于是烂尾至今。几年前韩生子曾想买下这块商店和炮楼,出价2.4万元,不知为何没买下,现在买不起了。”刘小东在8月26日的日记里写道。
时间即是艺术
刘小东有这样的习惯:每次出外写生,都会记详细的日记。并且,几乎他每个阶段的创作,都有影像资料留存。这次《金城小子》的展览,就由三个部分构成:除了26幅画作,还有刘小东的两百多篇日记、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监制的同名纪录片。
刘小东与电影导演之间的交情与合作由来已久。1992年他与当时的未婚妻、后来的妻子喻红主演了王小帅的首部电影《冬春的日子》,这部电影也主要根据他的个人经历改编而成;同年他还担任张元的电影《北京杂种》的美术指导;他画过《挚友张元》《张元向宁岱求婚》;1995年的画作《儿子》取材于张元的同名电影;2000年的另一画作《自古英雄出少年》取材自王小帅的电影《十七岁的单车》;2004年他与王小帅一起在贾樟柯的电影《世界》中客串两个新富人物;2005年他邀请贾樟柯去三峡拍一部关于他的现场写生作品的纪录片《东》,直接触发了贾樟柯拍摄《三峡好人》的灵感,2006年《三峡好人》一举夺下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2010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两周年祭日,刘小东在被保留下来的地震废墟里画《出北川》,场景也被导演王小帅摄入名为《等待》的短片……
他喜欢走出画室,在现实的空间里写生,那种在光影变化当中对人物与风景的捕捉,既艰难又过瘾。画《温床》,他把画布拿到三峡大坝与泰国曼谷;画《十八罗汉》,他在大陆和台湾的军营里分别搭起画架;画《易马图》,甘肃盐官镇的马市旁便搭起他的简易帐篷……他画画的过程,本身也成为一个景观,就像舞台上的一出戏剧,“如果这个时候有第三只眼睛去看,很荒谬也很有趣。所以我邀请他们来,不仅是拍我,而且也是拍社会发生的事情,永远有第三只眼睛在观望。人们都想表演,生活、现场、我在画画、他们在干他们的,这种景象如果你换一个眼光看是非常有趣的。”
看与被看,共同刻下这段时光的印痕,艺术家自己也无从躲藏、无法逃遁。刘小东说:“时间本身就是艺术。”
“我”已经不再重要
纪录片《金城小子》长达62分钟,执镜者是侯孝贤挑选的青年导演姚宏易,音效、剪辑、作曲依然是侯孝贤的固定班底杜笃之、廖庆松、林强,甚至朱天文都曾到金城小镇帮忙。
电影以维瓦尔第的《四季》配乐,处处流露出对时光的感怀。最初和最后的镜头,都在刘小东父母的家里。耳背的父亲,唠叨的母亲,一只小狗。饭桌上,母亲向儿子“告状”:看你爸的裤子,烧了八个窟窿!老父亲笑笑:不多,只烧了四个……他常常把夹着烟的手随意搭在膝上,然后忘记了抽烟这回事。
这是30年来,刘小东对父母最长久的陪伴。他在日记里写:看着他们,也像看到了老之将至的自己未来的生活。
“年岁大了,‘我’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刘小东对记者慨叹,“过去想出名,‘我’是第一位的,现在我觉得‘我’是一个越来越可耻的词,共同光荣才是美好的。这也是我通过和侯孝贤团队的合作,看他们片子体会到的。”
侯孝贤、朱天文、姚宏易等等来自台湾的摄制组成员,给金城人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刘小东说,从他们身上,他看到了“老派中国人”的神髓:“谁都知道人生而不平等,但要有一颗平等的心,对待你接触的人和事。毕竟艺术是希望使社会变得更美好一点,应该有大善。从他们身上我看得非常明显,对生命的尊重。这种观念下会使得片子很有人性。台湾人不像我们大陆—大家都变得复杂了,他们比我们要单纯,而且更加善良、更加善意。整个片子拍了以后,金城和他们接触过的人都觉得他们太好了。”
侯孝贤团队的拍摄方式是永远隐身在人后,尽量不影响被拍摄者的生活,“他不像个大导演。随便到饭馆里买一瓶二锅头,就在那儿和人喝上了,没有任何的隔阂。”电影里有一个场景:刘小东把画布搬到了朋友郭强开的卡拉OK,朋友们尽情欢唱、喝酒,他在包厢里光怪陆离的霓虹灯下为郭强画像。侯孝贤与金城小子们在镜头中唱得声嘶力竭,跳得大汗淋漓,刘小东画到中途接过麦克风,也吼了两首歌。这一刻,画与被画者、拍与被拍者似乎真的融为一体,实现了平等的“共同美好”。
然而,好景不长。10月的一天夜里,一个醉酒者驾车猛力撞向了刘小东搭在平房区巷道间的帐篷,帐篷里有他未完成的一幅大画。那个喝醉的人仿佛充满了仇恨,几次倒车,几次朝帐篷冲击,终于画毁篷倾。街坊邻居们议论:他应该认识刘小东。
醉酒者被警察带走了。警察对刘小东说,只要损失超过五千元,就可以要求赔偿。刘小东问:“如果损失超过两千万呢?”警察答:“那他就得判刑了。”刘小东最终选择了“零损失”。
这次意料之外的事故,提前终结了刘小东的返乡之旅。那幅画布撕裂的半成品,现在正摆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展厅里,同样参与记录着千万身家的名画家刘小东,与故乡金城间无法切断的关联。
本网站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及音视频),除转载外,均为时代在线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协议授权,禁止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 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转载使用,请联系本网站丁先生:news@time-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