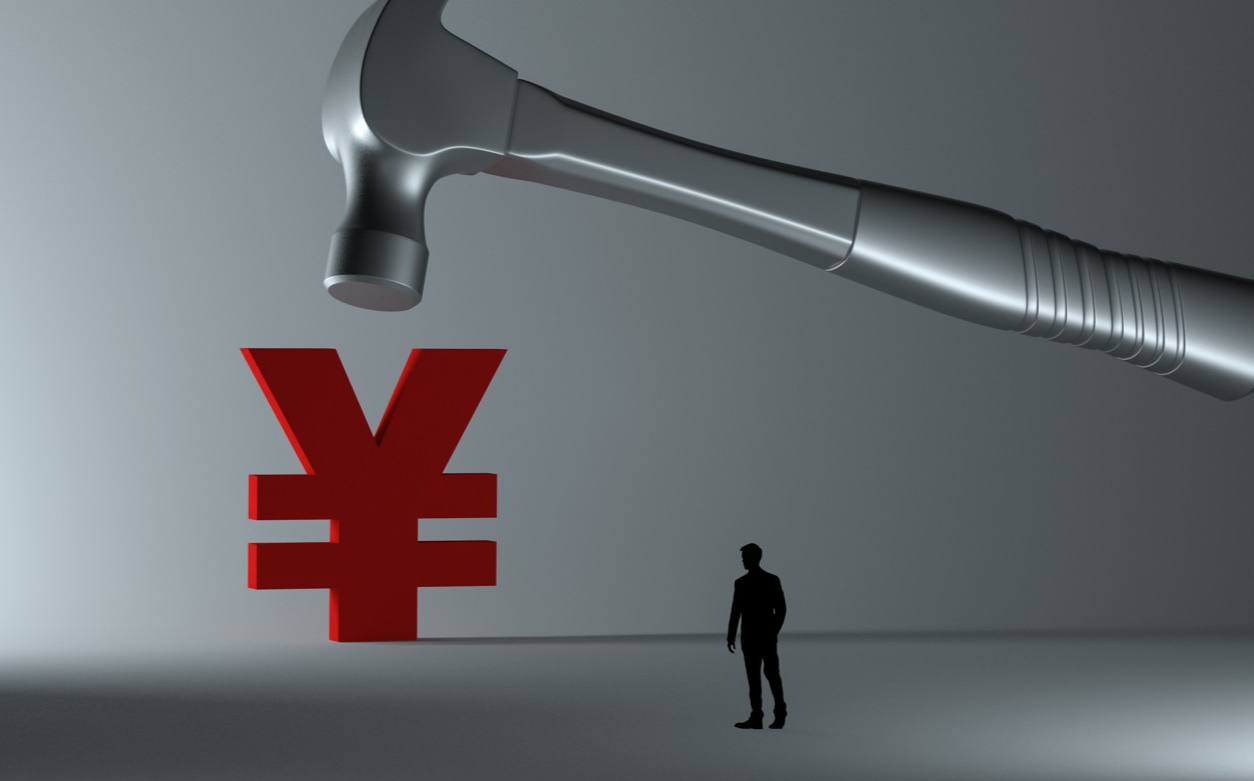宋庆龄在1949:可以自由呼吸了
2009-10-03 23:57:09
来源: 时代在线网
1949年,由于宋庆龄身份的复杂与微妙,她不可避免地成了各派政治势力博弈和争取的对象。这一年,她的心境大致可以用“悲欣交集”四个字来形容。这一年,她很累,且多病,上半年,宋庆龄几乎是在病榻上艰难度过。先是重感冒,继而是剧烈的神经痛、高血压,更难忍的是严重的荨麻疹,她每遇过度紧张和过度劳累,此病便缠绵不去。大夫令她卧床休息,并放弃所有的工作和活动。可她有时候却不得不勉力支撑,从床上爬起。在致友人的信中,她也曾这么直截了当地表示过复杂心情:悲者,由于蒋介石的独裁和颟顸,致使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国民党委顿败落,远引小岛。欣者,乃是和平已将降临,国家又有新的开始。惊心动魄的家信
1949年,国民党对宋庆龄的纠缠是多重的。年初,便有谣言说她将在国民党政府中就职,为此,1月10日,宋庆龄以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名义发表声明,称“孙中山夫人今天宣布:关于她将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职务的一些传说,是毫无根据的。孙夫人进一步声明,她正在以全部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救济工作。她是这个中国福利机构的创始人和主席”。
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李宗仁就职伊始,即派员持函赴沪,访宋庆龄,力劝宋参加南京国民政府。2月2日,李宗仁亲赴上海,拜访宋庆龄,请她以个人身份到北方一行,向中共领导转达他“谋求和平的诚意”。宋庆龄拒绝了他的要求,断然表示:“德邻先生,我曾经明白表示过,在国民党未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以前,我绝不参与这个党的任何工作。”此后,她在致王安娜的信中说:“我们中一些有远见的人曾经想努力避开这种结果(我两年前的声明可以作证),但历史正在选择一条破坏极大的、痛苦的道路。”两年多前,即1946年7月22日,宋庆龄对中外记者发表了《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希望在宪政的基础上,建立民主政府。
5月19日,上海的解放已指日可待,宋庆龄收到了她的妹妹宋美龄和弟弟宋子良的来信,信中云:“最近,我们都经常想起你,考虑到目前的局势,我们知道你在中国的生活一定很艰苦,希望你能平安、顺利。如果我们在这儿能为你做些什么的话—只要我们能办到,请告诉我们。我们俩都希望能尽我们所能地帮助你,但常感到相距太远了,帮不上忙。请写信告诉我们你的近况。”亲情的温婉、局势的大开大阖与政见的隔阂,使得这封言辞普通的家信有了别样的、惊心动魄的意味。时代周报记者在图书馆里查询了大量的资料,没有找到宋庆龄的回复。可以想见的是,她在读这封信的时候,心境一定是非常复杂与悲凉的。
在上海迎接解放
就在国民党对宋庆龄纠缠不休的同时,共产党也在积极争取与关怀这位著名的民主人士。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宋庆龄,电文中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嘱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
该电报是附在中共中央发给香港的方方、潘汉年、刘晓的指示电之后,并要他们设法转送给宋庆龄的。中共中央在指示电中指出:“兹发去毛周致宋电,望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意,万一金不能去,可否调现在上海与孙夫人联络的人来港面商。”周恩来审改电稿时加上:“总之,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两份电报均由周恩来修改审定。
接中共中央1月19日邀请宋庆龄北上的电报后,方方、潘汉年、刘晓进行了认真研究,决定派地下工作者华克之执行,计划先把宋庆龄接到香港,然后同何香凝一起北上。华克之秘密携带信件,潜赴上海,通过宋庆龄秘书、柳亚子的女儿柳无垢,把信件交给宋庆龄。据华克之事后回忆:“对于完成这一任务的细节与可能遇到的问题,潘汉年都预为设计,详细介绍,反复交代,要求保证宋庆龄的绝对安全。”“那次,我完成了送信的任务,并取了宋庆龄复周恩来的英文手书回港复命。”
对此次邀请,宋庆龄复函周恩来,告知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复函谓:“接获大札,敬悉伟大的主席和全党同志对我的关注,至为感激。经长时间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根据我的预计,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请勿念。”
2月20日,宋庆龄又复函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函谓:“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的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高血压,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
显然,当时宋庆龄并不愿意离沪赴京,一是因为病,二可能有着难以言说的复杂的心理原因。
5月27日,上海解放。28日,宋庆龄在寓所对著名大律师史良说:“解放了就好了,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在致王安娜的信中,她兴奋地表示:“感谢上苍,现在我们总算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小小的遗憾
然而,小小的遗憾发生了。就在那几天内,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一个营进驻林森中路(现淮海中路)后,某排排长奉连长指令,去武康大楼对面一所宽敞房子宿营,他们不知道这是宋庆龄的住所。门房拒绝解放军进入,双方争执喧哗,排长发话说:如果下午4时前不把房子腾空,将派士兵来搬走东西。宋庆龄闻声下楼,说:“我是宋庆龄。这里是我的公馆,你们部队不能住。要住,请陈司令打电话给我。”
陈毅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批评了师、团干部。他亲自打电话向宋庆龄表示歉意,并派人到宋庆龄住所去慰问,随即又与潘汉年一起亲赴宋庆龄寓所当面致歉。
5月31日,在陈毅、史良以及长期在沪从事情报工作的吴克坚的陪同下,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和第二书记饶漱石再次登门致歉,并派卫兵在宋庆龄住宅警卫。
虽然宋庆龄已多次表示不愿北上,但中共仍没放弃希望。6月19日,毛泽东在致宋庆龄的信中写道: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6月21日,周恩来亦致信宋庆龄,云:“……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6月25日,邓颖超带着毛周二人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国是的亲笔信,在廖梦醒(廖仲恺与何香凝的女儿,曾长期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的陪同下,抵达上海。到沪当晚,邓颖超没有贸然上门,而是派廖梦醒先行探访。
廖梦醒身穿灰布制服,头戴灰布军帽,走进了宋宅。宋庆龄一下子没认出她来,廖梦醒叫一声“Auntie”,她才恍然大悟。廖对宋说:“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接你,大家都盼望你能参加新政协。”宋庆龄迟疑良久,为难地表示:“北平是我的伤心之地,我怕去那里,待我考虑考虑,想好再通知你。” 1925年,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平,故宋称其为“伤心之地”。
两天后,廖梦醒再赴宋宅说服。言谈中,宋庆龄颇感盛情难却,再次表示“考虑考虑”。当晚,宋庆龄设宴请邓颖超吃饭。宋的态度似乎很是热情,但邓颖超知其孤傲的性格,不敢唐突,所以在这次宋邓初谈中,双方仅限于寒暄,没有言及北上之事。不过,看到宋的热情态度,邓颖超已经初步判断,请其北上“或有可能”,但“依其性格,尚需下工夫”。
北上的专列
6月30日,邓颖超向宋庆龄出示了毛周亲笔邀请函,宋庆龄终于答应北上。
在这几天内,为了此事,邓颖超与周恩来多有电报往复。在7月1日的电报中,周恩来要求邓颖超 “应多往孙夫人处谈话,为之讲解各种情况和我党政策,并对我军解放上海后,由于不熟悉情况,致对孙寓所及孙中山故屋发生几次误会,予以解释和道歉”。他又说,长途旅行,宋庆龄病体难支,“可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由浦口直开北平,并附餐车,大约三天可达”。
为了能让宋庆龄愉快地北上,周恩来对她提出的一切条件均予以满足。为了让她在北平住得舒适,周恩来亲自在东单的方巾巷,挑选了一座小洋房。据去过那里的廖梦醒的女儿李湄描述:“那是一栋外国人建造的两层花园洋房,小巧玲珑,在北京很少见这样的洋房。”
8月26日,宋庆龄坐上了北去的专列,8月28日下午4时15分,列车缓缓驶进北平火车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等50余人在车站热烈欢迎宋庆龄。毛泽东特地换上一套平时不大穿的,只有迎送知名人士时才穿的浅色衣服。车刚停稳,毛泽东便走上车厢,与宋庆龄握手,并说:“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宋庆龄高兴地说:“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毛泽东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宋庆龄说:“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
10月1日,宋庆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随同毛泽东等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
此后,她经常往来于北京与上海之间,她戏称去北京是去“上班”,来上海则是“回家”。而且她喜住上海。
餐厅变成卧室
在这一年中,宋庆龄的主要工作,她精力的主要投入点还是慈善事业。由她创立并担任主席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在过去的两年里,在上海进行的一项儿童福利计划,已惠及15000名儿童。她在写给友人的信中称:“这是我们通过‘小先生’制而实现的。‘小先生’制度就是培养一批儿童,再让他们把学到的文化知识教给上不起学的儿童。我们在上海的工作有三方面:群众扫盲教育,免费医疗结合卫生教育,分发救济物品。看到儿童们渴望学习,并愿意把学到的知识传授给更不幸的儿童,的确是令人鼓舞的。”此外,“在中国北部,包括30座国际和平医院和7座医学院的工作计划正在不断扩展;10所托儿所工作也在非常有效地进行”。
然而,由于战乱频仍,1949年初的上海,百业凋敝,民生艰难,仅1948年12月,在上海街头就有5000多人因冻馁而死。1949年春,上海街头的流浪儿童越来越多,宋庆龄极为不安,大力救助冻馁儿童成为她心头一件大事。长期以来一直支持中国福利基金会的美国援华会,也于1948年11月23日作出了“结束”的决定。为了“帮助解决中国目前过渡时期的紧急需要”,宋庆龄强支病体,运用自己的私人关系,给友人们写去大量信件,继续为中福会争取捐助,用于救助流浪儿童。有一度,她的家中甚至住进了4个小孩子。在给王安娜的信中,宋庆龄写道:“我现在觉得我像狄更斯的小说《圣诞欢歌》中的老吝啬鬼那样,4个孩子搂着我的脖子,把我的餐厅变成卧室。”
“三毛乐园会”
1949年春,遵照宋庆龄之意,中国福利基金会同张乐平联系,希望他举办“三毛原作展览会”,在会上举行义卖,救济上海街头流浪儿童。张乐平十分感动,立即一口答应。3月底,宋庆龄安排借汇丰银行礼堂举行预展,邀请一些中外朋友前来参观,并亲自出席。张乐平后来追忆这唯一一次与宋庆龄的会面说:“那天,宋庆龄坐在我的旁边,她当时已年近60岁,看上去却不过40岁的样子,衣着朴素,仪态大方,举止端庄。同外国朋友谈话,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同我讲话,却是一口道地的上海话。她很亲切地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家庭情况如何,怎么画起‘三毛’来的,等等,完全是亲切的家常式的谈话。外国朋友同我谈话,宋庆龄亲自翻译。开始我还有点拘束,看到她这样和蔼可亲,就很快自然起来。她一再向我表示感谢,说:‘这次你为流浪儿童做了件大好事,真太辛苦你了。’听了这些话,我非常感动。”
4月4-9日,“三毛乐园会”、“三毛原作展览会”在大新公司(今上海第一百货商店)4楼开展,并举行义卖活动。活动非常成功,共募得银圆3206元。
从北京回沪后,宋庆龄继续开展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在此之外,她还承担了“新的责任”,譬如为12月在京召开的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从事翻译工作和编辑材料,撰写文章,为此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忙得“足不出户”。然而,她时刻挂心的还是慈善工作。11月9日,她致函王安娜,谓:“关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在确定它未来的职责之前,必须先召开一次会议,以讨论总的救济事宜。也就是说,1950年初,我们必须开会讨论全国的救济工作及其重建事宜。……我渴望这次会议早日召开,因为救济工作确是当务之急,我们必须通力合作,尽快开始工作。”在信中,她也忍不住诉苦:“ (回上海后)没有得到一刻安静或休息。希望11月15日后能够继续输液,以便每次能够在长达8小时多的会议上坚持到底!”
自此以后,直到去世,宋庆龄始终专注于慈善事业,这是她人性关怀所在,亦可借此屏蔽政治纷扰。
共和经典文本
“24年前,孙中山先生把他衷心的愿望遗下给我们,要我们和中国唯一的友人苏联亲密合作。我们一定都记得,他曾怎样欢愉地迎接十月革命,热烈地主张和中国共产党合作。24年后的今天,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政治权利完全在人民手中,我们公务员的职责就完全起作用了。不像欧美政府的职责是政治和职能的一种结合。人民具有直接控制政府的权力,每个公务员都是本行业的专家,结果就是一个高效负责的政府。”
—宋庆龄
本网站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及音视频),除转载外,均为时代在线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协议授权,禁止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
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转载使用,请联系本网站丁先生:news@time-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