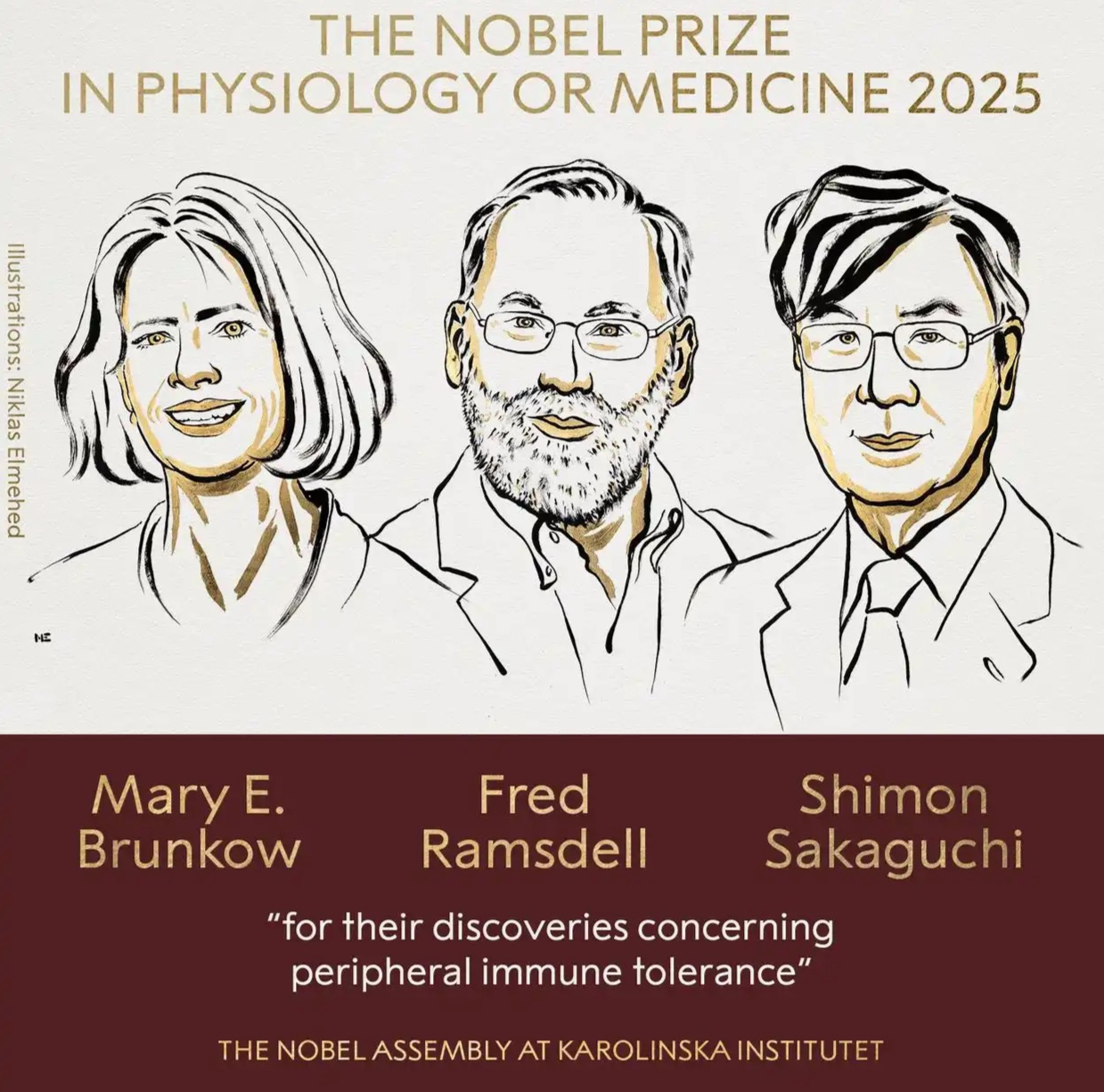《王的盛宴》:这不是一个狗血的故事
导演陆川强调自己“不是在讲一个很狗血的故事”,他说:“这个电影很容易拍得很狗血,乌江边上啊,霸王别姬啊很容易很狗血,我们要舍掉这一部分,因为我们讲的是一个权力的东西,实际
本报记者 谢培 实习生 赖宇航 发自北京
11月19日,距离《王的盛宴》最终上映时间还有10天。下午2时许,清华大学大礼堂1200个座位几无虚席。名为“《王的盛宴》上映倒计时”的活动预定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多小时,主持人许戈辉首先登场,开场白是“让大家久等了”。她不仅是为活动延迟而致歉。在陆川拍摄《南京!南京!》时就已筹备的这部历史剧,去年3月开机拍摄了整整8个月,上映日期一延再延,能否公映扑朔迷离。距离杀青整整一年后,陆川剪出的第17版《王的盛宴》终于能够敲响面世倒计时的钟声。放映完预告片,导演携主演刘烨、秦岚、吕韦来、何杜鹃穿过狭小的后台,来到前台站定。
台下,陆川“川制作”工作室负责人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三天前,也就是11月16日,《王的盛宴》才拿到象征着真正过审的“龙标”,一句“久等”实不为过。
“这个电影很容易拍得很狗血”
许戈辉提前看过全片,她对《王的盛宴》的评价是“一部看了之后可能让人改变‘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作品。对于现场绝大多数没有看过该片的媒体人和学生而言,最能关注的则是《王的盛宴》中提前曝光的极具现代感的台词。许戈辉鼓动刘烨和秦岚在现场重现了剧中刘邦被吕雉揭穿私生子时的一幕—他先是大义凛然道“我在外面干的是大事,灭秦”,又信誓旦旦说“绝对没有”,证据确凿后的解释是“我(他妈)喝多了”,最后他低下了头,嘟囔着“我错了”。
在电影院里,观众会为此而笑场吗?他们一定在这里看到自己或者朋友。陆川说,既然绝对无法还原2000多年前人们的语言,那么只能相信恒久不变的人性,从人的角度去探究他们的感受与反应。
“以2000多年前楚汉争霸为时代背景,通过十多位历史人物之间命运的交缠,展现出权力与欲望对这些为生存而战的人们内心的侵蚀与影响”,这是《王的盛宴》片方提供给媒体的影片解读。活动结束后,导演陆川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强调自己“不是在讲一个很狗血的故事”,他说:“这个电影很容易拍得很狗血,乌江边上啊,霸王别姬啊很容易很狗血,我们要舍掉这一部分,因为我们讲的是一个权力的东西,实际上这才是最有价值的。”
当《王的盛宴》传出未能过审的风声时,开始有人猜测是不是其中的故事影射了我们所熟知的近代历史。对此陆川并不认同:“如果这样说,我觉得是把我(的初衷)说小了”,他承认“因为刘邦时代的很多事情已经湮没”,所以曾“拿现代的素材去反推刘邦的想法—权力在每个时代都是一样的”,但“本意并不是借拍刘邦去关注某段历史”。
好在审查方能理解陆川的真正用意。陆川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跟局里说我没有想去做这个的念头,要真想做我可以做得更露骨,但那不是我兴趣所在。”他感兴趣的是权力的规律性:“统治者内心为什么恐惧?游戏规则到底是什么?其实我没有想停留在某段历史身上,我的着力点是这个体系是不是出问题了?为什么历朝历代都是这样?翻遍《资治通鉴》,里面写的都是同一个故事。我可以因此来推论刘邦当时的情况。”陆川说:“我想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不能再这样了。”
陆川觉得《王的盛宴》最终的上映时间还“挺有意思”:“我本来也不是为了今年拍的,原本应该年中就上了,如今被推到了这个时间。”
“现在公众还没有看到(电影),一旦看到公众就会觉得,我们真的去面向历史的时候,历史会呈现给我们它的规律,如果这种规律能够早一点被我们获得,也许我们不需要走那么多弯路。”
“我们电影很多年没探索了”
活动上,陆川指了指身边的刘烨、秦岚、吕韦来、何杜鹃,说:“这是一部由年轻人创作出来的电影。”
陆川生于1971年,刚过不惑之年。34岁的刘烨,在《王的盛宴》中从48岁的刘邦一路演到头。与刘烨同岁的沙溢,扮演了汉初三杰之一的萧何。除了扮演项伯的李琦和扮演范增的陶泽如,历史剧《王的盛宴》的主演都是70后、80后,其中最年轻的虞姬扮演者何杜鹃,年方25。
例如刘烨演刘邦,资方就曾有疑惑。他们担心年轻演员压不住阵,但陆川坚持了自己的选择。也许在他看来,年轻人是《王的盛宴》不重蹈近些年已“臭大街”的古装片覆辙的重要保证?陆川说:“一开始说要拍《王的盛宴》,就有朋友惊讶地说,你要拍古装片?有一个记者给我拆字,古装片现在就是:古,装片。”
陆川想要的是全新的东西。在活动的前一天夜里,时代周报记者在“川制作”工作室里提前看了《王的盛宴》,其极致的风格让人印象深刻。“为什么不做得极致一点呢?在自己还年轻的时候,要勇于去尝试。我不觉得观众会讨厌这种尝试,(平庸)可能是把观众当傻瓜的潜台词,我觉得观众可能会很惊喜,因为现在大部分观众都受过良好教育,我相信他们在电影院看到一部新颖的电影时,会去帮你传播这个电影,而不是去封杀它。”陆川说,“我们当初做这部电影的一个核心,就是要让电影行业多一种声音,多一种探索。当年第五代出了那么多导演,是因为他们在集体探索。我们电影已经很多年没有去探索了,我就想,能不能去探索一次?在内容上创新一次?”
最终将与观众见面的《王的盛宴》,有着随处可见的考究与精心,保持了从始至终的强大张力。这或许会更容易让年轻观众保持兴奋并投入其中。这种“刺激感”是逐渐修磨而成的,陆川说:“确实之前的版本会比较松,时长两个半小时。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这电影说白了还是讲关于权力规则的东西,我希望在能保住电影最想说的那句话而不丢分的情况下,让观众接收到影像的、剧情的,或着说信息的频率要高一点,我不希望它们被慢慢地消磨掉。当下很多电影还在谈剧情,这不错,是一个传统的道路。但现在电影更应该用信息和受众分析的角度来看。我希望单位时间给你的信息刺激、视觉刺激更强烈。”陆川说,一些看过片的朋友说《王的盛宴》和其他电影很不一样,也曾提到看得“很辛苦”。他反问:“如果把电影弄得很缓慢、很松,是不是就好呢?”紧接着他自己给出了答案:“显然不行。”
“很多真相永远隐藏在黑暗里”
媒体对陆川和刘烨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王的盛宴》将和冯小刚新片《一九四二》同日上映,是否担忧?陆川说,和《王的盛宴》同档期上映的除了《一九四二》还有李安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齐聚的华语大片“让这个冬天很温暖”。刘烨则用了“悲壮”这个词,他笑着说:“我又没说是《王的盛宴》悲壮。”
陆川是否寄希望于年轻观众?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觉得我的电影其实恰恰适合各个年龄段的观众,尤其是老年观众,五六十岁的。最近来了一些专家(提前看片),都是五六十岁的,你会发现他们感触特别深。但是老年观众也有可能一开始选择不看《王的盛宴》,因为他们会觉得这是大明星(拍的)电影。”陆川觉得,这次《王的盛宴》和《一九四二》可能都会遭遇误读:“我估计很多年轻的孩子们可能会冲着我们的片子来,因为有吴彦祖、刘烨。然后老年观众会选择去看《一九四二》,但恰恰可能老年观众看我们这个片子更合适。当然,也会有很多年轻人去看《一九四二》。”
另一个让陆川担心的“误读”,是对《王的盛宴》持有“古装片”判断的观众们,他一再强调这部电影的当下性:“现在制作方、媒体分析电影市场都是依靠现有资料,有没有大明星、好故事、好档期?但为什么有的电影这些东西都有,还是卖得不好?因为它们跟中国没关系,跟当下没关系。我觉得老百姓希望看到跟当下中国有关的,现在好多人还以为《王的盛宴》是古装片,他们看到之后会知道,这是对中国当下要说话的电影,是对中国未来要说话的电影。它不是说当下的政治,而是说我们当下的人,人性。”
活动现场挂着八幅《王的盛宴》角色版海报,在刘邦、项羽、萧何、韩信等人的身旁,都有着这么一句话:“很多真相永远会隐藏在黑暗里。”在更引人注目的大海报中,这句话消失了。陆川说:“因为它一波三折,我们不是很敢大张旗鼓地(说),总是欲言又止的感觉。我们想要提示观众,不要拿它当普通的古装片看,它和历史有关,它和秘密有关,它和认知历史角度有关,但是又没办法去说太透彻。”
陆川到底想对当下的人们说些什么呢?他对时代周报记者打起了这样的比方:“比如说报社,报社里也有刘邦,报社里显然还有萧何,外面采访的记者可能就是韩信。”说到这,他笑了笑:“这不是我在挑事,意思是说这种角色分配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被划定了。因为《史记》已经把这个案例挂在那了,后世一直在参阅它,把它当作成功案例来效仿。所以一旦出什么事,首先物理清除。它定下了一个特别不好的标准。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的案例,譬如刚完成的美国总统选举,奥巴马获胜后,罗姆尼向他祝贺。我觉得应该制定一个规则,在权力的角逐之中真正发光的应该是那个规则,规则折射出的是宽容,是人性。”
刘烨:翻身之作
本报记者 谢培 实习生 赖宇航 发自北京
(刘烨将《王的盛宴》视为《那人那山那狗》、《蓝宇》、《巴尔扎克和小裁缝》之后自己的代表作。 本报记者 郭杨 摄)
在“《王的盛宴》上映倒计时”现场,刘烨显得格外活跃。同陆川一唱一和,与记者互来互往,重现影片片段时自加旁白,末了还号召主创们“给大家鞠个躬吧”。
1998年,刘烨自霍建起导演的《那人那山那狗》出道,影留经典。2001年,凭借在《蓝宇》中的细腻表演, 23岁就斩获金马影帝,星途大展。一晃十多年过去,刘烨演出的电视剧电影排了长长一列。在《福布斯》中文版连续九年推出的“年度中国名人榜”(文体明星)榜上,刘烨的最高排位曾达到第20名(2004年),但2011年、2012年均落出百位。榜单并不是衡量一个演员价值的唯一标准,但从侧面佐证了刘烨这两年曝光率的急剧下降,这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他对《王的盛宴》的投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去年一年我什么都没有做,全部给了《王的盛宴》”。
如此专注,刘烨给出的解释是“再也不想让自己后悔”,他说自己已错过陆川两次,一是拒绝了出演《可可西里》,二是在《南京!南京!》拍摄至三个半月时因为各种原因“半路逃跑”,当陆川为《王的盛宴》再度找到刘烨时,他毫无条件地交出了自己。
刘烨的好心情延续到了时代周报记者对他的专访中。说得真诚,讲到自己的焦虑和自豪时都毫不掩饰。聊得随性,谈及表演时即刻配以身段眼神。他很容易让你感觉到,和明星的光环相比,刘烨更看重作为演员的价值。
“最困难的是台词感”
时代周报:陆川说要“将摄影机搬回2000年前”,作为演员,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刘烨:最困难的还是台词感。不能太现代,不能太随意,对演员来说是这样。我坚决不喜欢只要一是古装片,不管演什么年代都是这样,说话都是这样的(边说边演),我特别不喜欢这样。别说是2000年前了,你看100年前我们刚有照相机的时候慈禧的一些照片,那还是皇家的呢,一个个灰不溜秋,耷拉着肩。拍到普通人的时候,一个个都黑的,头发乱糟糟的。2000年的物质可能变化了,但人性是很难变化的。人为什么那么多年才能从树上下来呢?才能变成人呢?这样去思考,还是随意一点,但是“随意”这个度特别不好把握,随意大发了感觉像看玩笑,但不随意呢,就感觉自己进入不了状态,感觉是在“装”古人,观众自然也感觉演员是在“装”古人。这个对演员来说是最大的困难。
时代周报:你演的刘邦在青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有特别大的差别,特别是身体语言这个方面。
刘烨:楚汉太多事儿了,“分我杯羹”也拍了。当时项羽和刘邦两个人对峙,项羽以要煮了刘邦老爷子来要挟刘邦退兵,刘邦把项羽气得嗷嗷的,一箭射过来扎在刘邦胸口了,从那之后刘邦身体就每况愈下。人在受了那种重伤之后,成了王,人就开始那范儿了。我们当时连疤都做了,但那段戏最后没了,大家就一直没太在意—把老爷子的戏删得一点都没有了,挺不公平的—原先我们的点是,刘邦中了一箭之后,头发就开始花白了,残忍跟冷就开始了。
时代周报:这是你投入时间最长的一个角色吗?
刘烨:对,八个多月,第一次拍这么久。《南京!南京!》拍了三个多月我就跑了。
时代周报:这八个多月对于你自己来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刘烨:我觉得就是让我踏实了很多,但不足够。我这踏实不是说要更出名还是怎么样,而是这些年我一直挺着急的—从有了《英雄》开始,国内电影突然开始(赚钱了)。以前拍《巴尔扎克和小裁缝》、《蓝宇》那会儿还没觉得电影能赚钱,但这之后初衷就变了,初衷变了追求的东西可能就变了。你看我拍戏也十几年了,这些年我一直觉得不好意思,我一说还是那几部电影。在国外给别人送礼物的时候,也还是送这几部电影。但《王的盛宴》是我觉得终于可以送出手的了,到老的时候,我还可以和孩子说“我以前当演员时候还拍过《王的盛宴》,演刘邦”。
但《王的盛宴》还不足够,我觉得再有个三部吧,或者说不干了吧,我就真踏实了,我就能对自己选择这个职业有个特别好的交代。我觉得这是特别大的意义,能够留下属于自己的人物,自己的表演。
时代周报:比以前感觉更“定”了一些?
刘烨:哎呀,我就觉得到这儿(指演《王的盛宴》)之前十来年真的没白干,有这样一部作品,将来肯定买一堆碟在家里。
演老年之后感觉融入了刘邦
时代周报:陆川在这部作品中作出了不小的探索,你为什么伴随、支持他这个探索?
刘烨:任何事口说无凭。我看到《可可西里》之后就后悔没接那个戏,《南京!南京》我只看到我那个角色死了之后,但已足以让我后悔,我想我当时要是坚持到最后,电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我那时想陆川导演可能以后不会再跟我合作了,因为这是两次伤害。但这次又合作了,我得干。这部电影可能会有人喜欢可能会有人不喜欢,但肯定会留下来。他的才华不是学院派的,学院派的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陆川很特别,他的才华不一样,来源也不一样。第一次跟他合作的时候还会产生不信任感,但看完片子觉得他确实有料。
时代周报:你离开《南京!南京!》剧组的时候没有看到小样吗?
刘烨:没有,当时就开始怀疑。当然这是一方面,但最主要我觉得我是被教育得特别好的那一代,民族主义一点就着,我就那样,我接受不了。后来拍《王的盛宴》我知道他是对的,(但)他想表达的东西拍摄的过程中我也抓不到太多。
时代周报:抓不到什么呢?
刘烨:这是之前的事了,《王的盛宴》拍到五六个月的时候,有时候我也怀疑有些东西是不是对的。我一开机就想和他讲,我说:川儿,我们每天拍的得有个计划什么的。如果是学院派导演你就能把计划看得很清楚,跟陆川拍了几次戏我就知道了,要这样那就不是他陆川了。陆川是在现场找(灵感),他和电影还有演员一起成长,他是这样一个导演。来源于现场更能打动人,如果是早就设计好的,去完成的时候就像是睡着的东西。在现场找灵感也是陆川的本事。
时代周报:什么时候开始感觉自己融入了刘邦这个角色?
刘烨:就是在老年之后,时间特别能看清东西。我们在项城待了五个月,在宫殿里待了几个月啊!几个月可以拍两部电影了,但我们就为了几个镜头在那待了几个月。一个月过后你就习惯了,两个月过去以后你就觉得这是自己家了。每天穿着戏服,拍不拍都是这样(比画一脸妆、头发乱七八糟的样子),就慢慢习惯了,好像变成你自己了。
时代周报:“鸿门宴”这场戏你是如何考虑的?
刘烨:“鸿门宴”拍了两部分,第一部分拍了十几天,就是刘邦在跟项羽解释,范增在旁边质问,喊着要杀啊什么的,这个是一开始就拍的,大家状态都不对,陆川把这部分全剪了。第二部分就是“项庄舞剑”,项羽带兵打仗,想杀一个刘邦太简单了,是生死之间。那就没考虑太多,尽量纯粹一些,不去想刘邦是一个有谋略、有勇气的人什么的,就是本能反应。对我来说,演员演戏的时候尽量不带太多背景,背景靠电影呈现,演员要纯粹。
时代周报:最终面世的版本,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刘烨:陆川给了电影中所有角色的内心戏。包括项羽小刀童这个角色。这些历史我们太熟悉了,也被太多地概念化了,但在这部电影里你能感受到他们的内心。譬如虞姬,我觉得就处理得特别好,那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真实情感,跪在那儿也不哭,也不难受,也不悲伤,也不绝望,就是这样一刀刺死自己(比画),你能感觉到这个人物是真实的。刘邦作为一个老帝王,在深宫大院的那种孤独—2000年前的人离我们那么近,现在的人的感觉和他们的感觉能够碰在一起,这是最能打动我的。
时代周报:离开《南京!南京!》剧组时你在城门那儿抽了一根烟。《王的盛宴》杀青时你是什么状态?
刘烨:杀青的时候我们在坝上草原,剧组从开始的时候四五百人,那时只有50个左右。八个多月,大家都太感慨了。夕阳在那边,剧组杀青了,但来不及有任何感伤,也不愿意表达感伤,大男人总不好哭鼻子吧。我和陆川第二天要去美国,要开八个小时车连夜回北京。当时我回房卸妆,陆川发短信说:“谢谢兄弟啊。”虽然简简单单,但我还是(感觉)酸了,我特别不喜欢酸了,你说一煽情怎么再见面?我就给他回了一个“大恩不言谢”。八个多月了,结尾特别不辉煌,结尾特别不隆重,结尾特别不丰富多彩,就拍一张照片,装作兴奋地喊两声。但是那种时刻会留在自己心里。
本网站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及音视频),除转载外,均为时代在线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协议授权,禁止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 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转载使用,请联系本网站丁先生:news@time-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