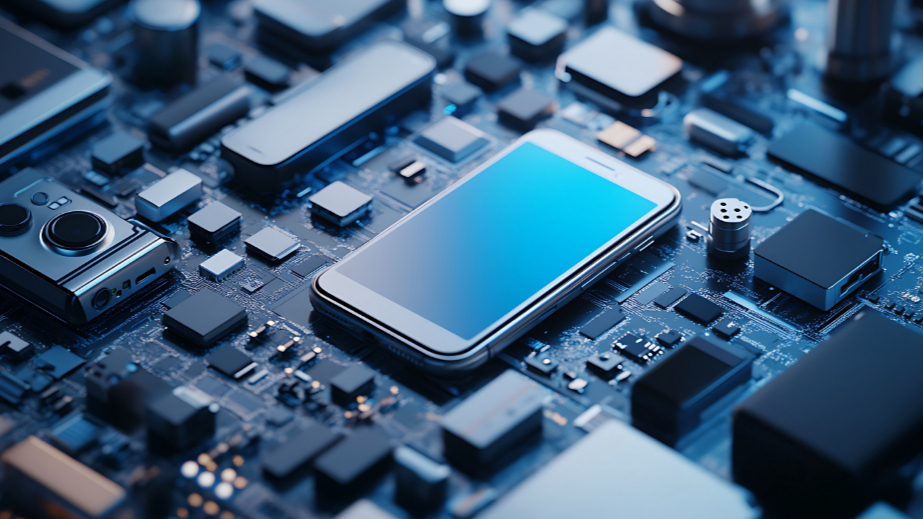庄重的抽噎:语言重建意义
福音书有云:“生命存在于语言之中,”语言是生命的居所,是一切隐秘事物的幽居地,也是爱和意义的诞生之处。诗人的作用在于激发出语言的某种独特的形式,使无语中的事物开始说话和表达自身,这即如对生命和爱的呼唤,以便和人内心对爱的渴望和牺牲付出的愿望相对称。在这两者交汇的雷电中,生命和诗互相被照亮,洞彻我们晦暗不明的存在。
蓝蓝
生活的漫画化是消除尊严的手段,不仅如此,它顺带解构了一切严肃思索所必需的东西—庄重、苦难、哀泣和羞耻心。它是滑稽小丑的舞场,是那些对自身处境无能为力者杯中自嘲的泡沫,是掩藏在笑声中沮丧的叹息。思想和艺术的漫画性,是一切变态扭曲时代最显著的美学特征。然而,向猛兽做鬼脸却并不是人类面对伤害和压力唯一的回应方式,即使是阿多尔诺提出对抒情诗的诘问之后—他不是也曾为没能和策兰会面而多有不安,甚至也修正过自己关于战后艺术的某些看法么?
坚持抒情诗的写作,说到底是从人的感受出发,抵达语言创造的真实。在此过程中,人的情感方式、亲历体验,尽管会分化为抽象的观念和理念,但抒情诗能够携带生活复杂感受、由此及彼以及从特殊到普遍的特性,依然能够通过语言将它们细节化和具体化,从而再次返回人的想像力重视和感受之中。没有哪个诗人愿意为苦难写诗,但这并不是拒绝诗歌的理由。在此,诗歌承担的是记录和见证的责任,为了那些人性中最微观风暴的呈现和意义的建设,《罗马尼亚当代抒情诗选》无疑是一个文本上的例证。
清算:从自身开始
就在马内阿写出《艺术家与小丑》的同时,他的罗马尼亚诗人同胞们在写着诗篇。这些不甘于接受低贱命运的诗人,在处理社会主义经验和个人生活经验的实践中,和许多东欧诗人一样,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们不再是那个登高一呼的领袖,不再是引领潮头的人,相反,他们走在沉默的人群中,分享这被迫的耻辱和痛苦,也共同分担沉默和对权力无奈的原罪。他们并未把自己视作无辜的人,从而拥有某种道德上的豁免权和优越感。不,对权力奴役带来的清算正应首先从自己开始,从日常生活和作为普通人的内心感受开始,那也是文明最基本的萌动。它要祛除思想和文字的漫画性,在被野蛮暴力和意识形态清空的内心,重新以语言建立意义和信仰,重新建设人的诞生—
“只用一击,/我就能将她杀死。/她朝我笑着,/微微笑着/……当我凝视她时/只用一击,/我就能将她杀死。(《害怕》,斯特内斯库)人的内心里藏着多少猛兽般的野蛮,面对一个毫不设防的人,诗人意识到这恐怖明确的可能性冲动,而这正是一切想要毁灭他人生命、控制并支配他人命运的根源,它不在别处,就在你自己的内心。它是潜伏在每个人身上的毒素,它直接导致了冰冷的虚无,哪怕这虚无看上去多么理性和冷静—在斯特内斯库的另一首《枪》中,对枪这件物体的物理构造分析得无懈可击,合理而充满秩序,甚至结尾的“开火”也干脆利落,唯独可以不去问作为一件杀人武器为何存在,它要射死的对象是不是像自己一样的人。此种习以为常的思维习惯恰恰是虚无主义在日常生活中的呈现—人们更愿意看到结果而非原因,甚至连结果也不重要,只是被动地接受现实,无论这现实是多么荒诞。麻木已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麻木的硬壳是我们抵御伤害的甲胄。不用费多少心思,我们便知道,这张硬壳下的生活已没有意义,生活和生命的意义早已被清空,它像吞噬一切的虚无—“一头动物走来/吞食岩石。/一只狂吠的狗走来/吞食石头。/某种虚无走来,/吞噬沙砾。”( 《充饥的石头》 )在一个没有良知的体制里,我们都是被虚无吞食的石头,直至我们也变成虚无本身,再去伤害其他的生命。没有意义的生命就是走动的坟墓,除了带来死亡别无它物。而诗人则知道“最后我走来/为了吞噬这个回答”,这一息尚存的火星难道不是意义的火种?
在斯特内斯库最打动人的《特洛伊木马》这首诗里,他写下了一个人是如何惊心动魄地与自己内心战斗的经历。这是一首充满悖论的诗歌,人性中各种力量相持不下,对自我的否定和肯定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自我的存在和自我不存在的相互侵占,自我之敌人和自我的肉搏,主体性的确立和对主体性的消解—这一切揭示出人是一个矛盾体的真实,这也是人性的胜利—没有什么比战胜自己更为光荣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比能够对自己清算反省的行为更让人尊敬。此外,斯特内斯库在诗的形式探索上也是罗马尼亚的领军人物,正如他对诗艺所表达的理想:“像婴儿的皮肤,像新砸开的石头/像来自死亡语言中的叫喊。”
判决:没有无辜者
“诗意并非物品的属性,而是人们在特定的场合中观察事物时内心情感的流露。”这段话可视作马林·索雷斯库写诗的圭臬。他正是从日常生活“特定的场合”捕捉观察自身和事物时闪电般的感受,并将此化为诗句,而这一切都是在专制统治、个人独裁背景下发生的—“每天晚上,/我都将邻居家的空椅/集中在一起,/为他们念诗。/倘若排列得当,/椅子对诗/会非常敏感。”( 《奇想》 )—排列整齐的椅子所隐喻的这个国家集权下人们的生活,已经被所谓的集体主义意识渗透到了物体的秩序,可想而知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控制力量,在此情形下,“绝对没有多余的激情”的“恰到好处的聚会”,只能是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的死亡的聚会,因而“不管怎样/这意味着/人人责任已尽,/可以继续/向前了”的结局,也意味着被恐惧清空的生活仍然在持续着麻木而可悲的惯性,它的目的只有一个—继续的死亡。索雷斯库痛感这种生活的荒诞和虚无,人们生活在谎言和屈辱之中,戴着各种不同的面具,那也是死亡的面具。作为一个尚要保留做人尊严的人,他拒绝承认自己是面具、是尸体,拒绝这样懦弱地生活下去—“我曾在所有文明的废墟上,/在成堆的写字板/和瓷砖上嚎啕大哭,/那么此时此刻为何/不在自己面容的废墟上痛哭呢?”哭,是悲从中来无法抑制的流露,是活着的生命的证明,他并未丧失疼痛感,他并未麻木如石头。当四周的人们渐渐接受并顺从充满耻辱的生活时,诗人能够发出的只有痛哭和叫喊,这是没有指望的生活中唯一有意义的声音,是对被奴役并在卑贱中可悲死去的命运抗争。
并不是说,一个诗人意识到对谎言的沉默、对独裁者歌功颂德奴颜婢膝带来的屈辱就可以豁免自己在此过程中被动和无奈默许所产生的原罪感。在整个专制体制形成的土壤里,几乎没有无辜者。坚持真理意味着直接将胸口抵住枪口,保命的策略带来安全的同时也带来了深深的羞耻和内心的分裂。对于诗人来说,判决迟早要到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从犯—“电车上的每个乘客 /都与坐在自己前面的那位/惊人地相似”,“每个人的颈项/都被后面那位所读的报纸 /啃噬。/ 我觉得有张报纸/ 伸向我的颈项/ 用边角切割着我的/ 静脉。”
不正常的社会败坏着每个人的生活,权力像细菌般毒害着人们,人们又互相毒害彼此,这是一个道德感彻底崩溃的社会的末日景象。人人都深陷自私的泥淖,追其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个恶性循环中,始作俑者不会想到,它所培养的除了懦夫流氓,还会有暴民恶棍,齐奥塞斯库被击毙的事件正说明了这一点。权力的罪恶链上,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其中的一环,这是真正的文明对人的警示,是诗人提醒了我们这一点。
重建意义:重视微弱的力量
“人间的非正义一般造成的不是殉难者,而是一些几乎下地狱的人。”西蒙娜·薇依这句话说的是伤害能够使人失去品格的结果。由于伤害带来的痛苦,人本能地对强权或同流合污,或以各种方式进行回击,其行为难免与原来他所反对的人如出一辙。正如法国哲学家勒维纳斯所认为的“伦理是第一哲学”那样,“为他者”即是生命意义的基本元素,也是对威权的反抗,因此,从语言开始重建伦理的意义也是诗人的天职。
杨·米尔恰在《模具》一诗中对于诗歌超越生活这一模态给予了意味深长的肯定:当诗人写诗的时候,纸张下的另一个人写着同样的文章,而当诗人停笔,获得独立生命的诗篇依旧在不停息地写着,“用古希腊语,用印地语,用正方形的希伯来语”。这里,写作行为本身就具有了意义,那是对时间的脱离,是对人类精神进入永恒的建设。诗人米尔恰·迪内斯库则明白,“他们打开了几座监狱/可无人从里面走出”,在地狱呆久了的人成为地狱本身,因而“我的体内已没有生命”,能够拯救人的泪水也变成了“一把刀子”。
瓦西里·丹说“诗是持久的磨难”,尼塔基·斯特内斯库说“诗是哭泣的眼睛”,毋宁说是人在生活中受苦,是在克服主体性以便与他者的生命相融时所遭受痛苦挣扎的真实记录,是爱在完成的过程中历尽艰辛的见证。福音书有云:“生命存在于语言之中,”语言是生命的居所,是一切隐秘事物的幽居地,也是爱和意义的诞生之处。诗人的作用在于激发出语言的某种独特的形式,使无语中的事物开始说话和表达自身,这即如对生命和爱的呼唤,以便和人内心对爱的渴望和牺牲付出的愿望相对称。在这两者交汇的雷电中,生命和诗互相被照亮,洞彻我们晦暗不明的存在。这一切有赖于精神敏锐的感知力,它只可能从人最柔软的内心里来,就像阿德里安·波乌内斯库的诗句那样—“雨水在写作/哀伤在阅读/微弱力量的坚强习性/便是趴在地上庄重地抽噎。”

《罗马尼亚抒情诗选》
索雷斯库等 著
高兴 译
花城出版社
2012年2月版
352页,36元
本网站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及音视频),除转载外,均为时代在线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协议授权,禁止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 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转载使用,请联系本网站丁先生:news@time-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