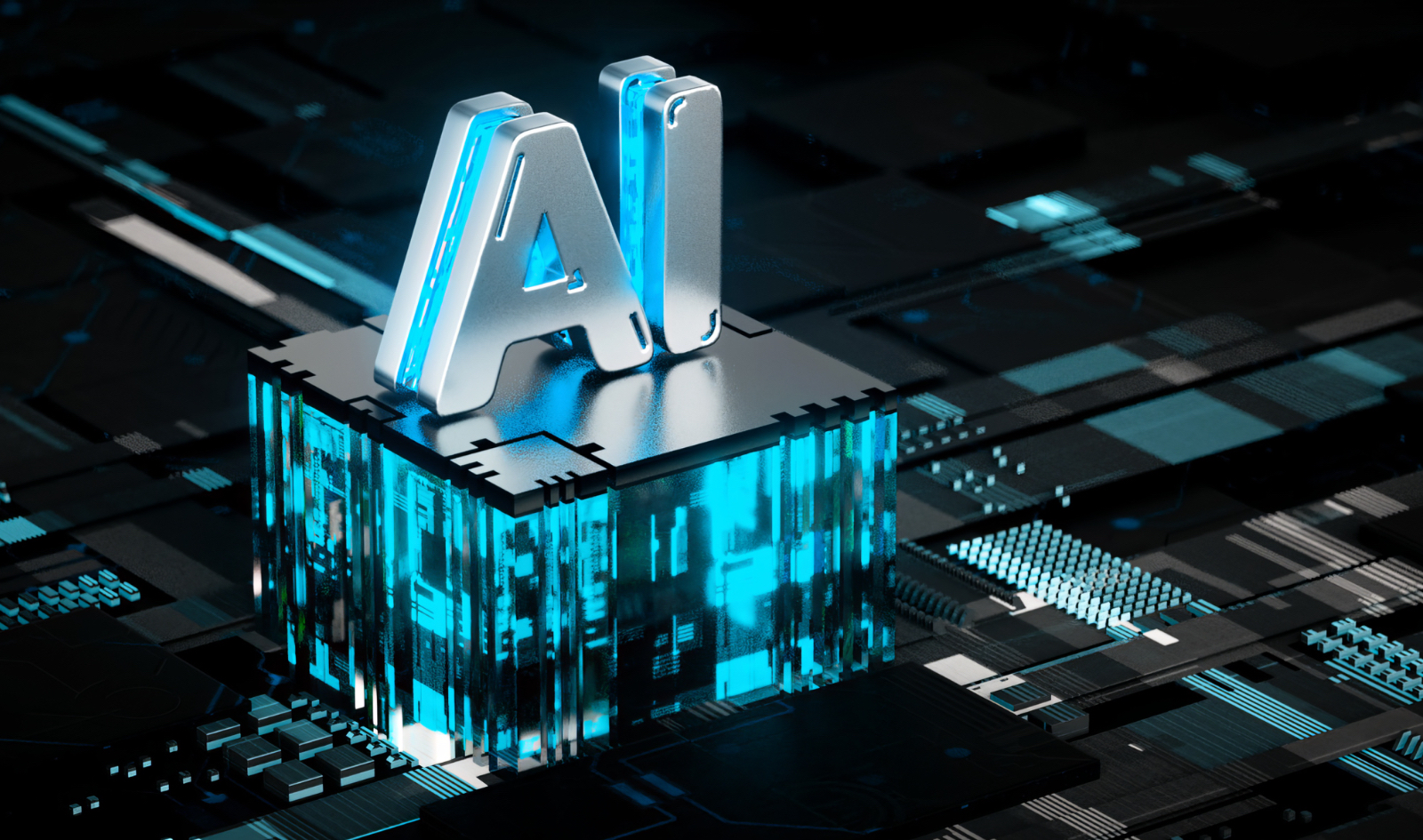韩寒与彻底坠入虚无的《1988》
曹寇
谈论韩寒是一件“危险”的事儿。因为当你赞颂这位新时代青年偶像的时候,容易遭致生理和心理上“双重老人”的反感,当你贬低韩寒的时候,众多的拥趸对你施行的群殴场面会让批评者感到难堪甚或恐惧—当然,有人乐于见到自己被群殴,在群殴中获得快感,这另当别论。这次,我想重点谈谈韩寒写的东西,以《1988》为例。当然,在谈文学之前,必须承认,韩寒已经成功,而且耀眼。
韩寒早已不再是一个少年作家那么简单的人物。近几年来,勇于在博客上对时事表达意见的韩寒,使自己的气场不再局限于“少年文艺”和“时尚写作”,而波及当代中国整个娱乐界和文化圈。敢言及其言论方式的某种机智,一度使韩寒成为媒体宠儿,进而被冠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头衔。
知识分子,多么有文化的一个词儿,还公共的,不给某个领域或集团代言,独立和民间实为应有之义,更显魅力。虽然李敖在谈到知识层面时,曾表达过韩寒“没文化”的意思,可惜李敖年老昏聩逻辑混乱,他忘了自己也曾年轻过,忘了自己曾写过《老年人与棒子》这样批判倚老卖老以老欺小的中国特有的文化生态的文章。多么不幸,李敖在年老色衰之际成了他早年痛骂的那种人。
韩寒究竟为这个时代提供了什么?我认为他提供的一种生活方式,显示了一种有价值的生活品质,起码对年轻人来说能够构成真正有价值的励志意义,而绝非唐骏式的可以复制的成功。成功是不可以复制的,韩寒亦不可能被复制,但韩寒没有唐骏的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文凭,这是正确和健康的。韩寒通过小说、赛车和编辑杂志获得了个人价值的呈现并被广为接受,这即是一种成功。
书店里贩卖着各种成功秘笈,那么成功是什么?王朔说“成功不就是挣点钱让2B们知道吗?”可谓一语点破这个时代最大的谎言—成功学。真正的成功恰恰是韩寒那样做自己想做的事,努力说自己想说的话。如果做不了或者说不了,那我们就保持沉默。在同龄人纠结于各种考试、招聘的时候,韩寒已率先驾车通过他的速度表现了生活的乐趣和愉悦。在路上的感觉真好!
在对一个成功者进行批评的时候,我们需要警惕余秋雨式的反批评。余秋雨面对批评,不止一次地告诉他的粉丝,那些咬牙切齿的批评者都是因为“羡慕嫉妒恨”才这么干的。之所以提到这一层,是表明我要在下文对韩寒的新作品《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提出个人的看法而提请免于受到这种反批评。
让我们来概览一下《1988》这本小说:和凯鲁亚克《在路上》一样,韩寒的这本书也是一本公路小说,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公路小说,因为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公路上。小说标题《1988》 正是“我”一路所驾的车名。或许是为了不使公路见闻失之于流水账,或许是为了使小说不致单薄,韩寒采用了两条叙事线索,即在公路见闻之外还均匀地插叙了少年记忆。其实这种小说结构并不新鲜,也谈不上创意,不过韩寒如此运用倒也恰到好处。寓意色彩浓烈,“我”驾着1988貌似漫无目的所赶往目的地,正是去找到那位当年帮“我”组装1988的朋友,换言之,“我”是带着作品去见作者。当“我”最终找到作者的时候,后者已作为一名死刑犯被刚刚执行,只能以骨灰的形式与“我”重逢;和这整个叙事流水相伴的是,记忆中的丁丁哥哥、10号和刘茵茵等少年时期的人物,他们也随着1988向前驶去及记忆的并行前进而“同期”死去,最后小说的地平线上依旧徒有“我”和1988形影相吊。也可以说,两条线索,二者有如公路两侧,构成平行关系,永不相交却又并行不悖、同速前进。
当然, 这仅仅是小说的经度,它的纬度则由一位名叫娜娜的怀有身孕的卖淫女与“我”一路同行构成。于是,娜娜的一切又成了另一条辅助性曲线,后者最终将生下的孩子 “礼赠”给了“我”,给全书画上了一个肉乎鲜活的句号:婴孩使前途貌似生机勃勃,实质则是忧伤茫然。
通过转述不难发现,构思颇有匠心,这绝非一部随意而为的小说。也许它还曾寄托了韩寒在小说方面的一定野心。据说这是韩寒最为用力、相对成熟的作品。事实上,如果能够耐心地读完,略去阅读过程的挑剔和不快,仅从概述来看,在掩卷的某个瞬间,它可能会作用于读者一种类似于马尔克斯《礼拜二午睡时刻》的震撼力。
然而我不能不诚实地说出我的真实观感:就《1988》看来,韩寒的小说水准还显幼稚。在情节驾驭层面和细节表现方面有着较为严重的欠缺。尤其在人物语言处理上,甚至显得笨拙和粗糙。个人认为,韩寒的文学修养并不高,就本书看来,他与一位缺乏训练、初涉小说的写作者并无太大的悬殊。可以负责任地说,在同龄人中,韩寒的小说肯定不是写得最好的。以小说作为语言的艺术的角度来看,这是一部并不优质的作品。
虽然韩寒试图使用在路上及妓女娜娜的一切来力撑小说的内容和批判现实主义色彩,但实际上,韩寒说得太多,见得太少,他对笔下描述的这些现实内容缺乏深入的了解,整个叙述因此呈现出力不从心的疲惫之态。
相比之下,另一条线索,即对“我”的少年记忆以及丁丁哥哥、10号和刘茵茵等这些人物的描述则显得靠谱得多。如果说记忆为虚,路上为实—记忆源自作者韩寒的个人经验,虚得到了相对真切可感的呈现,而韩寒的实比虚还要虚。这样一来,小说彻底坠入虚无之中,飘在空中无处落地。也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部不切实、不及物的小说,这恰恰与“在路上”这一小说方式所必须拥有的切实及物背道而驰。换言之,作为一部公路小说,《1988》是失败的。
《1988》这一案例再次说明了一个古老的写作规律:不奢谈艺术水准,单就手艺来看,写作需要学习和锤炼;当我们坐下来试图写一部作品时,我们的局限性就已经暴露,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我们的经历和认知是有限的,我们最好只写自己所熟知的事物和理念,也就是把自己的有限诚恳地记录和放大,而绝不是试图跨越有限而趋于无限。这大概是传统作家强调“生活”的重要性—“你有生活吗?”
无论如何,写作需要诚意,这一诚意就是忠诚和诚实。《1988》不算一部有诚意的小说。
就文字来看,韩寒显然不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刻薄一点说,韩寒在语言能力上还停留在高中阶段。如果他有志于当一名优秀的作家,这还需时日和努力。关键是,韩寒是否有此“宏愿”?中国是否缺少一位作家?
和诺贝尔文学奖无关,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当代文学的原始和粗鄙是有目共睹的,但即便如此,中国一点儿不缺少作家。这些作家依附于作协文联机构的文学刊物和形式各异的文学活动而生,或者依附于高校的中文系而活。他们的作品在圈内被有限度地传阅和评论,积极争取外加幸运的话,还可以获得诸如“某某文学奖”的荣誉。
可是,这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可以负责任地说,中国作家们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真相并非作家们所哀叹的那样,并非文学读者全部拜金和追星去了,恰恰相反,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文学阅读欲望有增无减。这些可敬的读者,他们从有限的生活费里挤出钱来购买各种书籍,在电脑时代,仍能挑灯夜读,多么感人的景象啊。可是当我们聚焦于他们手捧的图书,发现大多是译文作品。卡夫卡、马尔克斯、鲁尔福……这些遥远时空的大师居然才能满足他们对文学和审美的欲望。请问中国如此众多的作家,你们都写了些什么啊?!
还好,韩寒显然并非“中国作家”的一员,他不依附于期刊,而直接获得了出版商的眷顾。他无需文学评论家的鼓吹和赞美,自有成千上万的粉丝买账。
综观古今中外,这种相对的独立和自由才是一个作家真正需要的生态系统,经验表明,也唯有在这一健康系统内存活的作家才能向我们提供精神食粮。也就是说,中国确实需要一位作家,需要一位在独立和自由中向我们提供优质作品的作家。他可能是韩寒,也可能是别人。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
韩寒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0年9月版
215页,25元
本网站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及音视频),除转载外,均为时代在线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协议授权,禁止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 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转载使用,请联系本网站丁先生:news@time-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