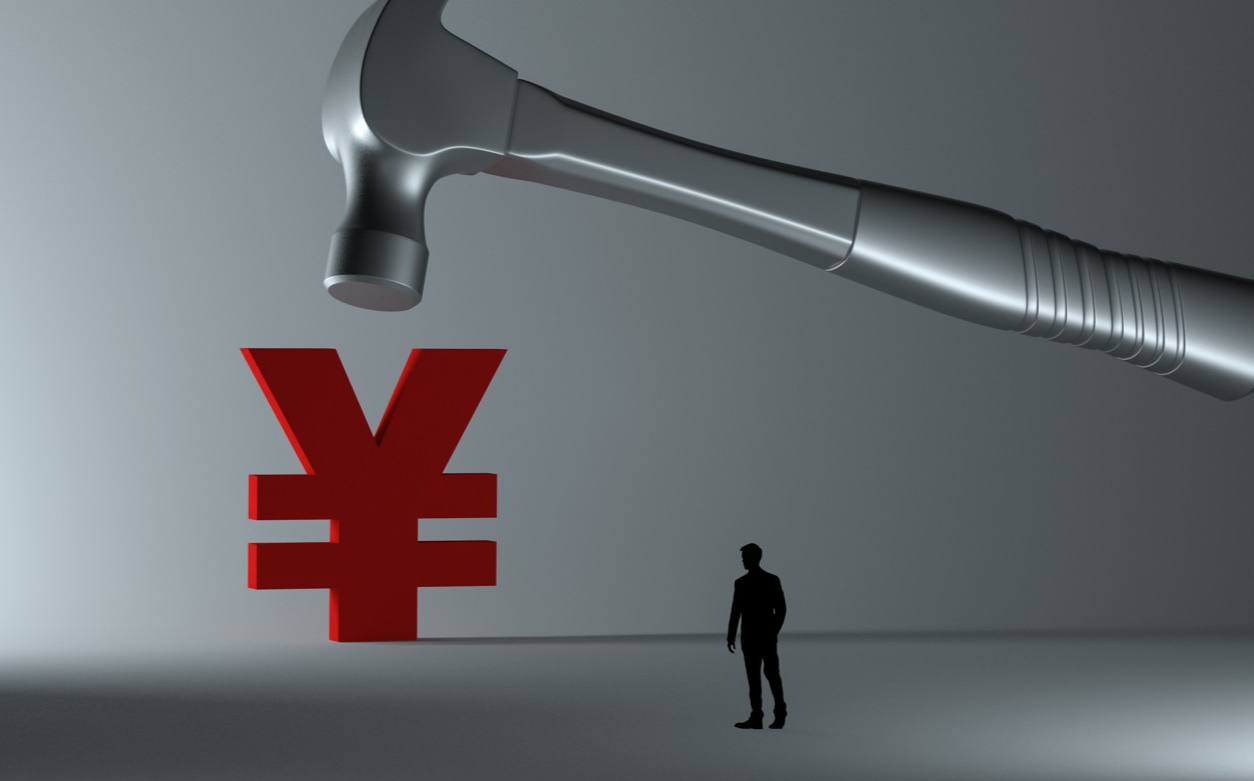《最爱》:这是一个诞生奇迹的时代
这部片子的剧情是生死恋,在他之前的作品里,爱情和理想都是时代的牺牲品,调子显然更悲观一些。“时代不同了,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奇迹都会发生的时代,爱情是可以发生的。”
特约记者 曹语凡
2011年5月10日,顾长卫导演的第三部作品《最爱》将上映。此前的一个春天下午,他在北京CBD万通中心一间小型会议室里接受了时代周报的专访。雨后的阳光在窗外银灰色楼体上闪烁,室内没有开灯,对顾长卫拍摄的电影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对自然光的偏爱。这位以“光线书写”而闻名于电影界的摄影师、导演,1984年曾在滕文骥导演的电影《海滩》里任摄影,拍摄中顾长卫大量采用以自然光来贴近现实的手法,曾给中国影坛带来不小冲击。而现在,暗淡的室内光线也恰好掩饰了他脸上略微有些局促的神情。
以往顾长卫见媒体,通常是由他的妻子蒋雯丽陪同,但这一次他是一个人。作为著名演员的蒋雯丽对他的电影也有不少影响,《最爱》里的一些桥段源于真人真事,就是蒋雯丽2002年以来帮助河南、山西艾滋病人这个特殊群体时的所见所闻。
顾长卫是个慢工出细活的人,这部电影历时三年,顾长卫一再强调说,“我确实反应比较慢,说话的语速也比较慢,想的事也比较慢,好在电影不是十分钟弄完的,所以还是有一点时间去选择、去比较。”随后他又补充道:“我这么说是为了安慰自己。”
《最爱》开拍之前,顾长卫把烟戒了。“一个人还有判断、有毅力去约束自己,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努力,”他说戒烟就是为了表现这个生活态度。在这部电影里饰演女一号商琴琴的章子怡曾说,顾长卫和同样是陕西男人的张艺谋都一样固执,这大约是对顾长卫的“毅力”的一种褒扬吧。
顾长卫曾被喻为“中国第一摄影师”,但媒体上居然没有一张照片好看过他本人,照片上的他眼睑下垂,特别是在漂亮的蒋雯丽身边尤其显得苍老。现实生活中顾长卫显得年轻很多,中等偏瘦的身材裹着件橄榄绿的夹克,脸上神情有一种沉静、内敛的感觉。蒋雯丽说当初喜欢他就是因为他很腼腆,他们相识于1989年顾长卫的生日派对上。
辉煌的摄影师时代
在顾长卫电影生涯的前二十多年里,一直是给别人的电影担当摄影师,与他同时代的张艺谋、陈凯歌这两位第五代导演标杆式人物有着长期合作。张艺谋早期作品几乎都是他掌镜,如《红高粱》、《菊豆》等,一度被喻为张艺谋的“御用摄影师”。喜欢在光影里捕捉力量的顾长卫在拍《菊豆》时差点和老谋子闹翻脸,他记得那天拍的是巩俐跟李保田的一场激情戏,中午开始拍,都布置好了,可他老觉得光线不对,想等到天色再晚一点拍。张艺谋非要赶时间拍,不肯妥协的他那天被老谋子提前支回了驻地。顾长卫特别想不通,觉得要是张艺谋做摄影师也会像他一样坚持,后来就想在饭桌上拍桌子。“真拍了桌子,剧组所有人肯定都傻眼,”顾长卫说,性格温和的他后来没闹事。那天张艺谋也看出了端倪,后来在吃饭的时候和巩俐一起过来找他,和他聊了很久,安抚他的情绪。
1987年与陈凯歌合作的《孩子王》让顾长卫捧回了金鸡奖最佳摄影奖,1993年再度合作的《霸王别姬》让顾长卫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摄影提名。几年后,他成为那个奖的评委之一,不过后来他又不动声色地放弃了。
陈凯歌和张艺谋是顾长卫早先在西影厂的同事,也是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同学,那时他们在一起做的“作品”是玩篮球、带女生偷白菜、在校园里捉麻雀、用气枪打老师养的鸡、办舞会和留长发。流行文化刚刚开始,作为摄影系学生,办舞会时顾长卫和张艺谋的任务基本是奉献型的,为跳舞的同学拍照和打灯。除了摄影,顾长卫那时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常常为师兄师妹免费理发。
顾长卫与姜文结识于老谋子的《红高粱》,姜文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时邀他掌镜,这部电影的色彩很惹人,充满了生命的张力和青春的肆意,此片让姜文捧回了国际上数个大奖。姜文说请顾长卫担当摄影师就等于为他的电影上了“保险”,在《鬼子来了》这部姜文的作品里,顾长卫用色非常极端,极端到只有黑白两色,摒弃了一切杂物和色彩干扰,空荡、寂静,体现了人物战时孤立无援的状态。
中国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中期最为经典的影片几乎都是由顾长卫掌镜,为他在国际上赢得了一定的名气。1994年拍完《兰陵王》,他携妻子蒋雯丽飞去美国闯荡好莱坞。顾长卫说他当时去美国有点游客的心态,就是想出去混混,顺便看看是否遇到更多有趣的片子拍。在好莱坞他拍过三部电影,最后一部是1999年陈冲的作品《纽约的秋天》,那是顾长卫作为摄影师拍摄的最后一部影片。
朴素的导演之路
电影始终是顾长卫表现自己才华的方式,张艺谋说,“顾长卫不会满足于做摄影,他会做导演的。”还是老谋子了解他,但好莱坞始终是电影人的一个梦,外面的世界可供一瞥,却始终遥不可及,做导演只能拍自己熟悉的生活。1999年顾长卫带着全家回国了,那时中国已经开启高速发展的引擎,国内的变化对他触动很大。
顾长卫的处女作《孔雀》正式开拍是在2003年4月,顾长卫用稳重厚实的长镜头,很直观地讲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个普通家庭三兄妹的成长。故事分为三段,姜文却用了“浑圆一体”四个字来形容这部电影。《立春》的故事背景是在1984-1994年这十年期间,这个时代也正是顾长卫成长中占重要位置的时代,故事拍得严酷而又朴素。《最爱》里赵得意和商琴琴的生死之恋的语境,是在当下这个爆炸式发展的时代背景中展开的,和前两部作品正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时代三部曲”。
顾长卫电影里的时代痕迹离不开早年作为摄影师合作的老搭档们的影响。他这样来形容张艺谋、陈凯歌和姜文给予他的影响:“你知道人家说读研究生就是和导师一起做课题,对我来说与他们合作让我有机会学习和经历很多东西。”
他对陈凯歌心怀敬意,“我永远也做不了那种宏大叙事的题材,”他说。顾长卫在他的电影里尽量展现自己对生命的理解,这一电影观念和姜文算是异曲同工。他说张艺谋身上的特点是值得他周围人学习的,“我觉得在我们很幼稚的时候,他就能看清一个问题的症结所在,总是能在电影上找到一个他独特的方式。”
而在本世纪初这十年里,顾长卫开始在自己的电影里有板有眼地走着文艺之路时,他过去的老搭档们的确在电影上又找到了新的“独特方式”:张艺谋先是拍了武侠大片《英雄》,后来还拍了《满城尽带黄金甲》和《三枪拍案传奇》等;陈凯歌倒是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宏大叙事”,《无极》之后又有了《赵氏孤儿》;姜文是商业艺术不偏不倚什么都要,电影元素多了许多花哨的玩意儿,《太阳照样升起》里硬是把泥土弄成橙红色,《让子弹飞》里把月亮弄大。
顾长卫的《最爱》是否能像他之前两部片子一样坚持以往那种沉静、朴素的画面和追求诚实的电影观念?有人说无论如何,作为“中国第一摄影”的顾长卫执导的片子画面一定好看。对此,顾长卫却不以为然:“不一定,因为这一回是亚洲第一摄影杜可风在掌镜,这人老High着,画面只是电影其中一个元素。在欧美,一般能获奖的电影都是剧情片,剧情很重要。”而这部片子的剧情是生死恋,顾长卫终于开口谈爱情,在他之前的作品里,爱情和理想都是时代的牺牲品,调子显然更悲观一些。
对此,顾长卫解释说:“时代不同了,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奇迹都会发生的时代,爱情是可以发生的。想想我们经历的各个时代,记得小时候在照相馆照相,师傅拿着红布条晃着说笑,被摄者笑的时候就照下来。然后,中国人照相说茄子,外国人说Cheers,我们就笑了。现在人说,你们家有什么,大家说有—钱!真的很开心,你不觉得这时代变了吗?你觉得仅仅是悲剧吗?我觉得不一定。”
专访顾长卫:电影里有我对生命的理解
![]()
(《最爱》海报)
特约记者 曹语凡
对顾长卫的专访非常顺利,不知不觉就聊了两个多小时,顾长卫也从最初的局促变得自然起来。其间一位工作人员走进小会议室打开灯,顾长卫的神情又变得腼腆起来,似乎无法承受白炽灯光直接照在脸上。
1999年从美国回来后,顾长卫和妻子把家安在北京,但拍电影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得呆在小城市或乡村,因为顾长卫电影的背景多半在那些小城市,他说也想通过这种距离上的处理,让作品有一种幻想的色彩。他出生在西安的城乡结合部,在他看来中国哪儿都是城乡结合部,住在城市里的人内心也同样处在城乡结合部。他尽力让环境更贴近人物的精神世界,另外,也是为了便于选择干净流畅的镜头视野。
在末世感中看待生命
时代周报:从摄影师到导演,两种行业中的哪一种更能体现你是顾长卫?
顾长卫:摄影师吧(毫不犹豫),因为做摄影师拍的片子更多,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像我。做导演要担当更多责任,人际关系对我来说更难一点。
时代周报:可是你最终还是把自己变成了顾长卫导演。
顾长卫:(笑)哎,慢慢来吧,我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关键是我也回不去了,我再回去人家也不要我了。关键是我也不太熟悉了,现在拍片也不用胶卷,还有,胶卷也都变了。我当摄影师拍的最后一部影片是在1999年,那都是上世纪的事了,真的变化好大,回也回不去了。
时代周报:近年很多影像方面的运用往往被指形式大于内容,你从摄影转做导演,你对自己执导的电影怎么看?
顾长卫:坦率地说,我对自己也挺欠缺了解,一方面对自己拒绝了解,我特别不希望我对自己有一个准确的评价,比如我的优点是什么,不足是什么,人都受了这么多年的关于怎么样成长和进步的教育,当你明白你有一些缺点和特长的时候,可能又有新的问题出来了。老是觉得我其实各个方面都比较晚熟,有些东西领悟得比较慢,个别时候我也会安慰自己说,哎呀,这样没准还大器晚成呢。
时代周报:慢工出细活。
顾长卫:可是有人说,大的作品都是一挥而就。
时代周报:这种气质适合姜文吧。
顾长卫:姜文也有慢工出细活的一面,他更有艺术家的洒脱和锐利,他做电影时有点强迫症,想到哪儿非得那样干不可。
时代周报:姜文曾说,现在的作者导演有点生不逢时。你对此有何感想?对当下这个“失去原创性”的电影时代作何感想?
顾长卫:我觉得姜文才是作者导演。
时代周报:你很喜欢提到“生命”这个词,你说的生命意味着什么?
顾长卫:比方说,《最爱》里其实有我对生命的理解,有我的取舍在里面。生命是什么,有时候觉得就像从过山车上下来,你多刺激、多兴奋、多疯狂地笑着,那么荒诞地笑着,紧接着就有一种害怕,我觉得这里面就有一种末世情结。在末世感觉中怎么看待生命,就像《最爱》里有一句台词,很典型的一句台词:咱们结婚吧,趁活着。我觉得是一种悲喜交集的态度。
趁活着,多做几部好电影
时代周报:你之前的两部片子是志在获奖的文艺片,再现了第五代曾有的辉煌,但是《最爱》里的全明星阵容,还有名导客串,是为了进军商业电影吗?
顾长卫:我没有。我不是一个特别有商业概念的人。坦率地说,我不是个太有追求的人,只想着做片子做得比较尽兴。如果拍摄过程的每一天都想到让电影变成钱,老去意识这一点我觉得挺为难我的。大家说文如其人,我总是想我拍的作品有个性吗,显示了艺术家的才华、那么的鲜活那么的独特吗?我其实担心的是这些。我相信我还是一个非常善意地通过电影去学着理解生命的人,所以也相信观众很容易接受我的电影。
时代周报:可是我们觉得你迟早也会走向商业大片的。
顾长卫:我觉得电影应该有一个更科学的概念分类,不要简单地分成商业片和文艺片,这对两头都不公平,特别容易误导。好像商业片就没有艺术成分,文艺片就一定不好看。最好是按国际上习惯的分类,比如动画片、喜剧、功夫片等各种类型,在这个分类基础上,然后再说每一种类型都有观赏性很强的、有质量很高的、有流俗一般的,我觉得这是不是有助于观众更容易找到自己想看的片子?这对做电影的人也是一种督促,你就是一个动作片,你就是一个喜剧片,你也会在这个类型里面尽量让自己做到最高品质,做到最精彩的内容。老是文艺片、商业片的分法容易产生偏见,一旦有品质,人家就说你是艺术片吧,接着就会带来一个负面影响,那就肯定不好看吧。其实每一种类型的电影里面,比如特别小众的、实验性很强的电影也有很烂的,商业大片里也有上乘之作。
时代周报:你的作品中人物总是把握不了在时代中的命运,有一种严酷而又朴素的现实生活语境,这是否也折射了你自己的人生观?
顾长卫:我常常觉得自己的个性和在现实当中有缺憾的东西,人常常愿意在作品中去呈现。比如我个人来说,我其实不够理想主义,所以特别愿意在作品里去描述一个理想主义者,也许很不现实,但它是作品关键所在。我觉得那是一个梦。
时代周报:再问一下,你为什么觉得自己不够理想主义?
顾长卫:我相信明天一定会到来,所以就不够理想主义,因为明天,比较科学地来说,无论明天怎么样它都会到来,所以也许缺少浪漫主义。所以趁活着,想多做几部好电影。
希望人们更关注艾滋病人群体
时代周报: 《最爱》里的爱情是否就是你自己的爱情观?你和你妻子蒋雯丽已经生活18年了。
顾长卫:爱情、家庭对任何人来说都很重要,可能我不是特别出息,比较宅男。在这部电影里有一些我非常欣赏的东西,留在心里的那种感受、那种形象,希望观众看电影的时候获得那种信息。电影是一种交流,当我们说都喜欢看一部电影,我们就能坐在一张桌子吃饭、成为朋友。
时代周报:你前面两部作品看完后总让人有种如鲠在喉的感觉,这部作品你觉得将会给观众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顾长卫:我觉得其实这个电影相对于《孔雀》和《立春》来说,可能会有更多积极的一面。它真不是玩沉重的,不是简单地往沉重、绝望方向去讲的。也不是轻松和幽默,我觉得试着去理解生命的美丽,试着让我们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数着我们生命的脚步。
时代周报:在拍《最爱》的同时你还做了纪录片《在一起》,在柏林电影节首映时,片中展现的艾滋病患者生活状态朴实感人,不少外国观众捧场。
顾长卫:因为那是真实发生的东西,特别有质感,都是活生生的人不是演的。开拍之前我们在想,如果找不到人怎么办,没想到他们会来。就是我们请到的三位艾滋病感染者—涛涛、刘老师和帅哥老夏。这就意味着我们一起住、一起吃、一起工作,一起混了那些日子,我们等于全体剧组的人都是志愿者,都是参与者。你想生活上的困难肯定有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几个工作人员在开始的时候知道这个情况就走了,我觉得他们也没错。单纯地讲涛涛他们有很多的无辜、很多的不幸,他们真的需要帮助,我在想,活动本身值得记录下来。
我担心片子出来后,他们未来生活也许会遇到不少的困境,如果是那样,我们预防艾滋病的路更遥远。到时候我希望更多的人关注。
本网站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及音视频),除转载外,均为时代在线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协议授权,禁止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 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转载使用,请联系本网站丁先生:news@time-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