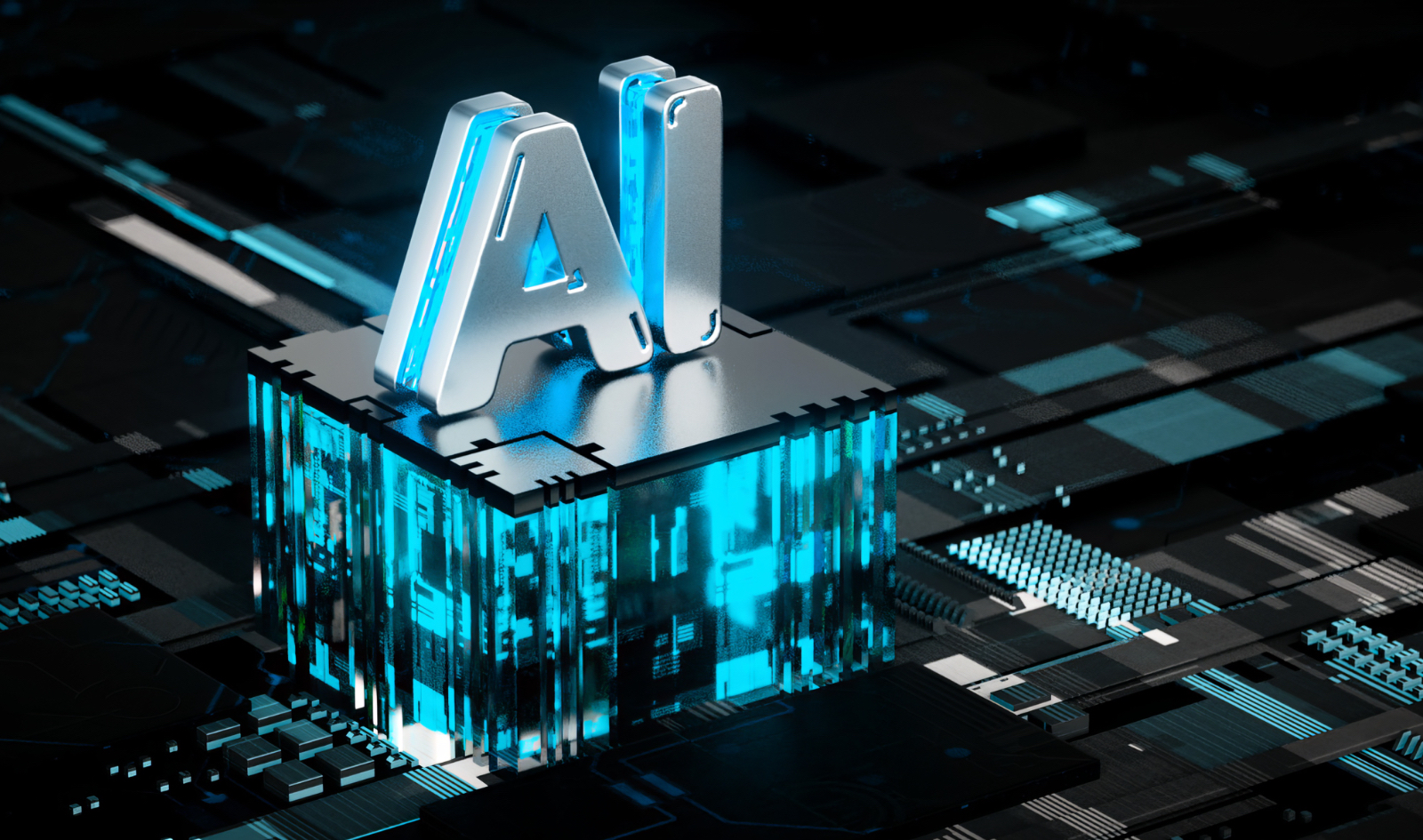“梁庄”:现代化转型中真实的中国农村
以非虚构的方式讲述当下中国农村,便是梁鸿作品《中国在梁庄》所做的事。有些中国在北京;有些中国在重庆;有些中国在西北;有些中国在沿海;但更多的中国在梁庄。
特约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2010年人民文学奖得主梁鸿说,自己是个狂热的文学阅读者。作为一位研究乡土文学的学者,她“每天晚上睡前都必须要看书,一定不是理论,而是文学作品”。
“许多时候,睡前阅读本来是为了更好入睡的,结果却激动难眠。”梁鸿对让她激动的作家、作品如数家珍,“有很多乡土作家,如阎连科、莫言、贾平凹、李佩甫、刘震云、杨争光,等等,他们都是我喜欢的作家。他们也都写出了经典的乡土之作,如《日光流年》、《红高粱》、《秦腔》、《羊的门》、《从两个蛋说起》等等。”梁鸿说。
但她自己的乡土写作,却与上述作家完全不同。2010年11月19日,第八届人民文学奖揭晓。梁鸿作品《中国在梁庄》获得非虚构类作品奖,随后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更是受到各界瞩目。中国“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对该书更是高度评价,称赞它描画出“最近三十年‘被’消灭的四十万个村庄的缩影”,“不曾认识梁庄,我们或许就不曾认识农村,不曾认识农村,何以认识中国”?
无论是奖项还是文体,“非虚构”文学对于国内普通读者都属新鲜事物。“非虚构文学并不是一个新名词。”梁鸿这样解释,“在西方文学中,它是一个很大的传统,经常占据图书畅销镑的首位。如果追溯一下它的生成,就会发现,非虚构文学的出现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生活和精神结构的剧烈变化有关。非虚构小说的出现是对社会危机的反应与象征,这很有点像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情形。”
众多的荣誉和社会好评下,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香港《亚洲周刊》2010年十大好书中对其这样概括:梁鸿认为,乡土中国不仅是地理意义的农村,而且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性。她批评当局“对自己的民族过于不自信,一切都想连根拔起,但乡村是否真的就适合用全球化、现代化的模式来发展呢”?
以非虚构的方式讲述当下中国农村,便是梁鸿作品《中国在梁庄》所做的事。《中国在梁庄》一书的封面没有任何修饰,只写了这样一句:有些中国在北京;有些中国在重庆;有些中国在西北;有些中国在沿海;但更多的中国在梁庄!
(梁鸿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现任职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文艺思潮研究。《梁庄》(成书后名《中国在梁庄》)获2010年人民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奖,《中国在梁庄》入选多个2010年好书榜单。)
写作故乡出于精神困顿
河南省穰县梁庄其实是梁鸿的故乡。
“写梁庄,不是出于一般的归乡,而是出于一种精神的困顿与痛苦。”梁鸿这样对时代周报记者总结写作《中国在梁庄》的目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学术生活被束之高阁,与现实失去了某种联系,我自己长期的研究方向是乡土文学和文化史研究,但对真正的乡土却似乎并不了解,这让我对自己的学术价值产生怀疑。”
梁鸿在《中国在梁庄》的开篇便表达了这种内心的困顿,她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甚至充满羞耻之心—每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似乎一切都没有意义。而另一方面,乡土中国、农民却在现实世界里越来越成为中国的问题,“我的故乡,我的父老乡亲,和千千万万个故乡,正成为整个国家的问题与现代性发展的‘阻碍’与‘病症’。”
“这让我非常痛苦。所以,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回到梁庄,是一种精神的必然。我想,中国当代的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在以不同方式回望自己的故乡,否则,真的难以在精神上达到安宁。”她说。
2008年和2009年的寒暑假,梁鸿回到了偏远、贫穷的梁庄。整整五个月里,她与村庄里人一起吃饭聊天,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庄的一切,找寻往日的伙伴、长辈以及逝去的亲人。但写作的准备,远远不止五个月的田野工作。
“其实几乎有十年时间,我每年回老家都会收集材料,但比较零散。另外,为了这次写作,我也做了三年的理论准备。”梁鸿阅读了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相关书籍,如《忧郁的热带》、《菊与刀》、《原始部落的性格与气质》、《乡土中国》、《江村经济》以及当代学者的乡村社会学调查如贺雪峰、温铁军、秦晖、吴毅、于建嵘等人的书,“我靠近书桌的书架上摆的全是这方面的书。有些我都看了不止一遍,也做了不少笔记。它们对我的启发非常大,增加了我对乡村的理解力。”
当梁鸿真正走进田野,走进曾经生活过20多年的梁庄,她忽然发现前期的理论准备最多只能在方法论上给予指导。“当面对一个个乡村生命时,他们的痛苦、忧伤、欢乐无法用某一种理论思想或某一种结构模式来衡量,来解释。”
这是一个文学工作者对乡土的关怀,它与社会学、政治学将农民看作某一个阶层、某一种符号不同。“在这里,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矛盾是以极其复杂的纠结方式呈现出来的。我要把他们作为一个个生命写出来。这一个个生命样态中所包含的信息可能会远远超出我的理论概括。当然,也可能因为我是一个文学工作者,我更擅长的是进入情感、人性深处。”
想沿着儿时玩伴的打工足迹走
梁鸿的《梁庄》,是一个个农民的生存故事。留守儿童、留守农民、农民工、乡村政治、农村的信仰问题……这些常常见诸报端的热点议题,在《梁庄》里成了老贵叔的控诉、建坤婶的愤怒、春梅的呐喊以及明太爷的叹息。
“这些主题并非之前预定好的。在回去之前,我对乡村也是一种模糊状态,只是经由家人的讲述大致知道一些故事。但是,在真正走进乡村生活之后,才发现,当代乡村所存在的问题远远超出我们可想象的范围,那些故事背后生命的疼痛,情感的渴求以及内在的颓败无法用一种笼统的叙述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梁鸿重新思考她的讲述,她说自己是不得不以问题的方式呈现。
“其实,就文学创作而言,这并非是好的选择。但是,正如我在许多场合所说的,在《中国在梁庄》中,我的目的不在怎样表现出我的文学能力,而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呈现他们的存在。”
《中国在梁庄》全书共八章,每一章基本呈现四个故事,一个主题。王家少年强奸了八十二岁的老太;昆生把自己的家安在了墓地里,即使火化了,也要把骨灰在棺材里撒成人形……梁鸿的叙述里有太多触目惊心的字眼,却恰恰是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梁庄。可是梁鸿还说,关于梁庄的故事并没有说尽。那一个个她挨家挨户听来的故事里,还有太多触动心弦,却最终未能呈现的故事。
“譬如书中小柱的故事,我只是简单讲了一下。一想起他,我就心痛。我们同年出生,是非常好的伙伴,他英俊,高大,开朗,最后却因肺出血而死。他究竟是否因长期吸入金属粉尘而导致死亡,没有人知道,最后也没有查出原因,当然,更没有人去承担责任。我真的很想沿着他打工的城市、工厂走下来,到他最后打工的那个工厂去调查。可是,中国有多少那样的工厂,有多少个小柱?”
讲述那么多农村现代化转型中的故事,梁鸿却并没有结论。“如果说乡村未来之路的话,我只能说,我没有结论,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状态的乡村存在,要想找到一条简单明了的路是不可能的。”
但梁鸿有她基本的看法,她说青年批评家李云雷评论便是其中一种。“《中国在梁庄》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向我们呈现了农村的这一状态,也即我们所面临的不只是政治、经济危机,而是心灵危机、伦理危机与价值危机,相对于政治经济危机,这是影响更加深远的危机。”
生活本身要比虚构更震撼
《中国在梁庄》一经出版,便有读者激动地评价说:“作为文学作品,它比余华的《活着》更加真实;作为田野调查,它比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更加人文。”与此同时,《中国在梁庄》更被一些人说成是另一视角的《中国农民调查》。
除了最早获得人民文学奖的肯定之外,《中国在梁庄》出版之后,这位文学创作的“新秀”迎来一片赞誉。香港亚洲周刊将其选为2010年十大华文好书(非小说)名单,更进入国内几乎所有年度好书的榜单。
梁鸿显然受宠若惊。“《活着》已是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而费老的《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也是社会学的奠基之作。我还远远没有达到他们的水平。但是,这样的比较可能恰恰说出了这本书的独特视角:以真实的笔触和人文的情怀进入乡村的现实与生命存在。”
梁鸿所说的“真实的笔触”,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她借鉴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对此,她解释这种方法应用于文学的初衷:“当代文学的整体结构太过封闭,作家在艺术与审美的怪圈里打转,却忽略了一点,也许当代生活本身要比虚构更为震撼,这个时候,需要田野调查来弥补个人生活的有限,同时,也更能发现事物的本质所在。另外,采取跨学科的视野会给文学带来新的角度和新的可能性,它会使原来被遮蔽的东西变为一种敞开。”
与“真实的笔触”异曲同工之处的是,梁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毫不避讳地说出了“中国作家们太自恋”的观点。对此,她对时代周报记者强调说,“还不只是作家,也包括如我这样的文学批评者和学者。”
“因为身份、价值的边缘化,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处于一种奇怪的巨大感伤中,其实,是被知识分子权力丧失的失落感所控制。因为这种虚妄的精英意识,这种感伤,导致一种深刻的自恋和精神的涣散,从而使当代知识分子失去了对公共事物和重大情感的关注能力。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不去思考我们的民族、我们自己在这场声势浩大、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运动中究竟失去了什么,究竟要面对哪些重大的问题,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不合格的。”她说。
“作为一位年轻学者,梁鸿走出书斋、走向故乡是为了使学术与言说回到坚实的土地与活的人生。现代背景中的故乡书写,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焦点之一,但《梁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仍显出迫切的意义。梁鸿以复杂多端的角色和角度,呈现当下的、具体的村庄,在忠直而谨慎的描述中,梁庄成为了认识中国乡土之现在与未来的醒目标本。”
—人民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奖的授奖辞声音尚未散去,梁鸿又回到了她的讲台、她的书斋,但是她贴近土地的写作并未结束。“如果有合适的题材,我还会写。但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对我而言,都是为了寻找通往故乡之路。”
本网站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及音视频),除转载外,均为时代在线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协议授权,禁止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 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转载使用,请联系本网站丁先生:news@time-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