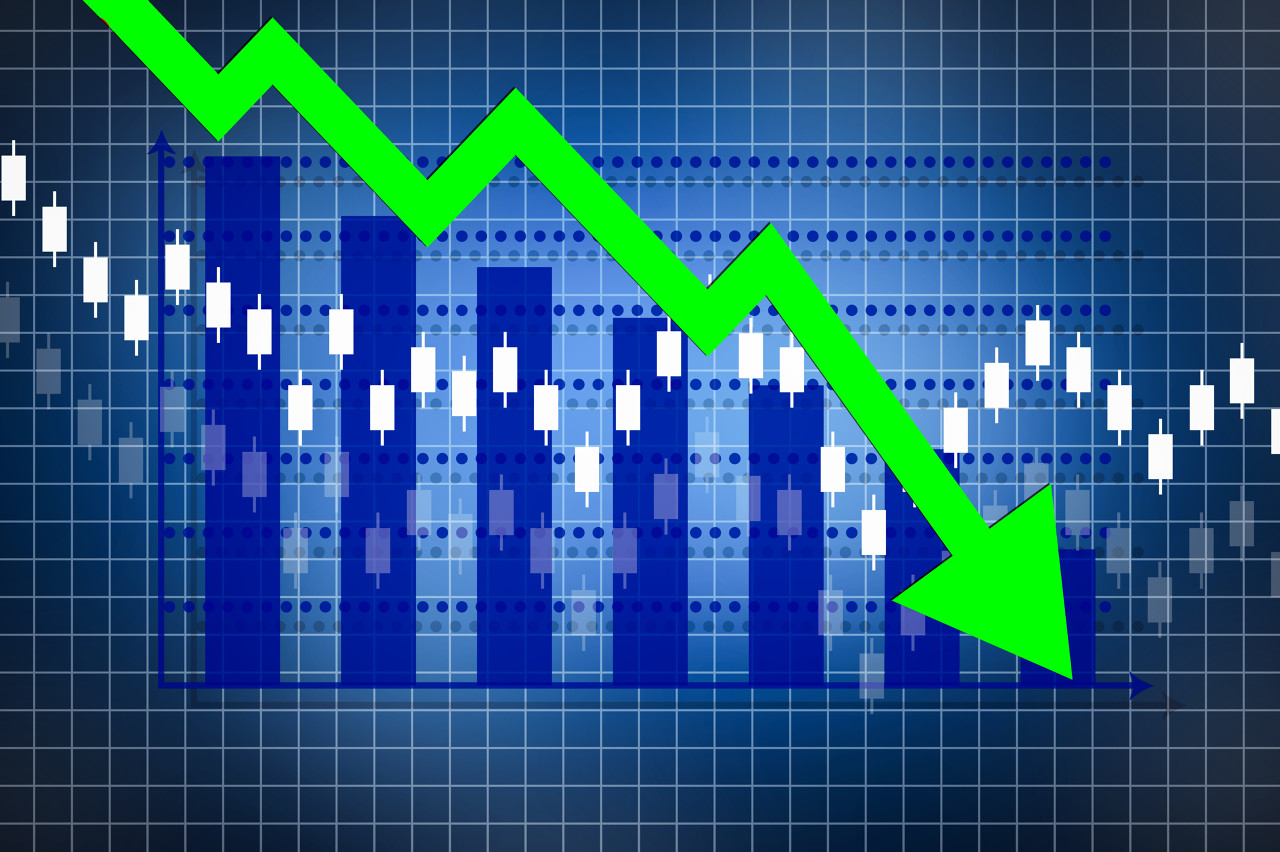中国学人在美国发现什么样的历史?
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的高王凌先生作为路思学者访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也正是在这一年,他与几位志同道合、有心改革历史学的年轻学者,一同开始酝酿筹建旨在交流学术的“留美历史学会”。1987年,“留美历史学会”正式成立。
二十余年过去了,当年负笈求学的留学生,有些已在美国史学界思考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历史视野和治学方法。也正是在这二十年间,中国学界经历了从上世纪80年代的西学热、方法热到如今言必称“中国模式”、“中国学术”的心态转变—抄袭事件屡见不鲜,学术批评公器难以建立。正常的学术批评往往被引向政治解决途径,学者比的是挣多少钱拿多少项目。
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在美国经历了什么样的学术训练和思考过程?对中国当下的历史学术状况有怎样的反思?作为两位为“留美历史学会”工作多年、对中美两国历史学界有切身观察的学者,高王凌、王希均有话说。
特约撰稿:雷天
受访者:
高王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王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
中国史学最大问题:如何建立与当下社会的联系
时代周报:1986年,高老师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当时为什么要筹划这个“留美历史学会”?
高王凌:当初我们有很大的心理愿望,就是不愿意再见到一个闭关锁国的局面,我们成立这个,最根本的就是希望保持一种内外思想学术交流。办这个历史学会,没有政治性,没有营利性。第一天开会我就得罪人,有位学者要讲国内怎么不自由,怎么受压制。我没让他发言。我说你不要讲这个,你就讲到了美国怎么自由、能干什么,
时代周报:余茂春教授在书里写了一篇文章,写当时参加美国历史学会的百年年会,兴冲冲去的,但发现历史学在美国的发展是一个“悲观”的状态。
高王凌:到底我们这批人出去是什么目的?有没有目的?最后将成为一个什么目的?这些都不好回答,但我们当时是一心向上、一心求学的,这个劲特别足,美国史是没有问题的史—人家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差不多可以这么说吧。
王希:该做的经典问题都被做遍了。
高王凌:不像中国史。但我们当时都在不断摸索,都在自我成长的过程里。中国史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它和当下社会的关系。中国史学应该怎么建立起和当代社会的关联,建立起对当下的关切?这个问题无论你搞多古代的—像巫鸿搞考古—实际上有一个当下的关怀问题。这在任何时候都不是简单的东西。
王希:美国史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很多新领域,对传统史学做出了挑战,种族史、妇女史、社会性别等等,打破了传统史学大一统的格局。新一代史学家在美国史领域内成长起来,出现了一种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碎化”的情况,传统的神话和大框架被打破。这正好也是美国史学换代的时候,
而我们这批刚去美国的中国学生,当时处在进入的状态,不太能够看清楚美国史学界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因为我们不在其中,我们并不需要与教授争夺资源;现在我们这批人已经进入这个体制内部了,有些人已经可以跟美国人平起平坐来争论了。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更深层次的争论。这里有一个阶段和认知差别的问题。
当时国内史学的发展还处在从“文革”中恢复过来的阶段。譬如,书中的邵勤教授和陈兼教授,出国前就小有名气了,一个研究中国古代史、一个研究二战史,都已经获了奖或发表了有影响的文章,但他们两人当时在出国前共同的感觉是国内已经没有人可以教他们新的史学方法,所以要去美国寻求新的研究方法。
高王凌:就我跟《读书》这一两年的接触,我批评他们,以前《读书》为什么办得好?因为那时候大家有一种渴望,“崇洋媚外”。几十年过去了,现在什么事不知道?你还来那一套,什么外国人怎么着的,中国人早腻了。中国人现在“自大狂”得厉害,什么都行,现在30年过去了,你不写点自个儿的东西,那怎么行呢?时代都变了。
考据派“光拉车不看路”,理论派贩卖“洋片儿汤”
时代周报:王老师觉得当时对自己影响、触动最深的方法论是什么?书里提到,当时罗荣渠教授用在中国最时髦的“现代化论”去美国大学做讲演,但基本上没什么反响,因为那个在美国已经过时了。
高王凌:那当然了,他做的时候就已经快过时了。
王希:我在国内是学外语的,所以我的史学训练基本上是在美国的学术体制中进行的,国内史学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是我后来反过头来读中国的史学著作才逐渐体会和感觉到的。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都觉得没有底气跟国内出来的历史学家讲话,因为我的确没有受过他们那样的训练,有些心有余悸。
我在美国上的第一堂课是美国早期史。美国通史我很熟,去之前就已经读完了,但美国教授讲的角度与国内很不一样,她一开始就讲种族、族裔和社会性别,用这种方法来分析早期史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这种提出问题的方法让我感觉到很新奇。这就是新社会史,研究的不是精英和帝王将相之类,而是移民、劳工、妇女之类的普通人,还会研究监狱的犯人和码头工人,真正的普通人的历史。我觉得这与我们传统学的历史很不一样。在国内,你往往只需要学会叙事,把材料编辑在一起,就可以写历史了。但美国人做历史的角度非常不一样,切入点也不同,组织材料的方法不一样,目的不是简单地追求讲一个故事,更多的是既要讲一个故事,还要把故事里面的含义带出来,美国人更注重解释和解读。诠释历史的意义实际上是一个思想者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在美国做一个历史学家,实际上是做一个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必须要有很好的文字功夫,要有思想,要有组织材料、搜集材料、解释材料的能力。历史学家的训练是全方位的,我对这个感触特别深。当然,美国史学界使用的方法非常多,有时候会使人产生眼花缭乱的感觉,让你无所适从,有的题目看上去似乎也没有什么意思,但你要仔细地看。
时代周报:高老师呢?
高王凌:有关史学方法论的问题—我不认为美国同行重视这个问题。
时代周报:中国重视吗?
高王凌:中国同行也未必重视,现在的国内历史学界是考据学派当家。就是做一些填补空白什么的研究为主,思想性的东西比较缺乏。
王希:国内注不注重历史解释?
高王凌:不重视。有人就管考据派叫“光拉车不看路”的,太尖锐了点,但也不无道理;那些理论派倒是讲思想,但他们的东西好多都是外国来的,我管这叫“洋片儿汤”。从“洋片儿汤”到“洋片儿汤”就没意思了,美国的东西其实是从哪儿来的?法国、德国。美国的好多东西就是“二道贩子”,咱们这边跟着闻风而动,这也不好。
在我来说,我的美国同行,比如曾小萍这些人,王希的老师,他就不认为理论是这些东西,什么是理论呢?比如中国人口多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你得说出点道道来,你得有解释,这就叫理论。张五常写过《佃农理论》,这就叫理论,不是“洋片儿汤”才是理论。在美国人那里头,理论是根本不值钱的,就是李零的话,“理论是敲门砖”,没用的东西,敲完门就没用了。不以方法领先,以问题意识领先。
王希:我很同意这个观点。我觉得我们好像对方法论有一个误解,我看国内的博士、硕士论文,前面都是有一个什么选题、意义,然后方法论。我记得看过一篇博士论文,其中提到要用三种方法,包括历史学的方法和国际关系学的方法等。实际上对方法论的理解有很大偏差。在美国的史学著作里面,你很少看到某某历史学家可以说我的著作用到什么方法。一般不会这样说的。我觉得高老师说得非常好,最要紧的是提出问题,然后围绕问题来准备和组织材料。
高王凌:对。我的法国同行主办一个年鉴学派的杂志,他看中国人的稿子,第一部分,“喀嚓”就撕去了,看也不看,从第二章开始看,法国人就这么干。说戴个大帽子干什么?
问题意识最重要,但是学不来
时代周报:两位刚刚都提到最重要的是提出问题。但是否存在这种情况:要在美国学界立足,得找到让学界认可的题目,尤其像王希老师做美国史的,好多问题都已经被做光了,必须得找一个很特别的角度去发现一个问题,但很可能这个问题并不是王老师关心的。
王希:这正好是我遇到的问题。我在《在美国发现历史》里写的基本上是我读研究生的片断。里面确实也谈到了写作博士论文时遇到的选题问题。
问题意识当然受很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个人背景、哪个老师、在哪个学校受的训练、阅读、关注的事物、个人兴趣等,都会影响问题意识的形成。我当时对“民主”这个问题感兴趣,与当年国内的大环境有关。民主是个老题目,如果只是单纯从体制史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去做,导师会提醒你说“这个题目很陈旧了”。你去找工作的时候,别人也会说,这个题目早已研究透了,滚瓜烂熟了,有什么新意吗?这样你可能找不到工作,美国学界是非常现实的。所以你必须要想办法提出新的研究问题,开创新的研究思路。我当时选了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与共和党的政治,因为它涉及了黑人的选举权问题,这是个宪政史上的问题,又涉及政治史,当然也与种族问题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是一个同时与美国政治制度和核心价值观构建相关的问题。所以你必须花功夫来想想这个题目,要兼顾具有经典意义的问题和具有现实关怀的问题,找到两者之间的连结点,将两者统一起来,提出新的思想,这就叫构建问题意识。
高王凌:其实(问题意识)这东西无法下手,学不来的,这个东西是在你内心里,跟你曾经的经历关系特别大。假如我根本没有插过队,没有在农村待过的话,怎么写农民?这些经历都“刺激”你。我原来想退休了以后再写(农民)这段,后来怎么提前了就不说了,但早晚这件事是过不去的,早晚要弄,它总要蹦出来的。
国内学术会议和小黄皮信封
时代周报:学术共同体和学术批评在美国的情况怎么样?在中国,拿人文社会科学来说,一般各个学科都老死不相往来山头的学者好像也是不闻不问。
王希:美国大学的历史系一般会有一些定期的学术研讨会,同系的教授出版了新著,大家会为他举行一个学术研讨会,请他把新作用20分钟的时间讲一遍,大家提提问题,哪怕不是做他这个专业的人也来听一听,向他表示祝贺,。
高王凌:对,你是一个团伙嘛,你就要清楚他的学术研究。国内的情况是即便一个大学一个系,互相谁也不知道在研究什么。
王希:这是一个有形的学术共同体,另外还有一种无形的学术共同体,是通过学术批评的方式建立的。打个比方说,高王凌教授出一本书,本领域的学者们会来做评论,写书评,这是学者们必做而且也乐意做的一件事。一本学术专著出版之后,出版社请作者列出10个左右的学术期刊或对本书感兴趣也比较有信誉的报纸杂志,出版社免费把书寄送给这些刊物,由他们去邀请专家写书评。期刊怎么找人呢?高老师的书是讲18世纪中国土地制度的书,这本书送到了《亚洲学研究》期刊,该期刊会从自己的学者档案库中找出相关领域中出过类似专著的学者的名字,然后把书寄给他,请他写书评。被邀请写书评的人如果事先评审过这部书稿,或与作者本人十分熟识,应该提出回避,改为推荐他人。这样,10个期刊可能发表10篇不同的书评,也就有了比较客观的、多元途径产生的学术评论。作者可以对书评提出异议,可以反驳书评者的评论,期刊还要给书评者回应反驳的机会,并将双方的意见全部登出来。所以这是一种健康的交流。
高王凌:那个批评性很强,不像我们一写都是“抬轿子”。
时代周报:比如我写一本历史方面的学术书,寄给10位专家,那些专家凭什么要为这个书写评论呢?
王希: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们在美国做很多学术工作,都是没有报酬的。如果出版社请你审稿,说明你有一定的学术地位,是专家,人家才请你来审稿。为期刊或出版社审稿一般都是没有一分钱报酬的,甚至书出来后都不会寄给你一本。你可以在个人履历中写“我为某某大学出版社审过稿”,这就是很好的资历。为期刊写书评,期刊会将被评的书送给你。如果不写,还得把书寄还回去。
我回来后,遇到一些事,有一些说不清的感觉。譬如,你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或去做一个与学术相关的活动,做完之后,马上有一个同学或者年轻老师过来给你送一个小黄皮信封,里面装的是现金。我第一次拿这个小黄皮信封的时候,心里直打鼓,很不习惯,有一种犯罪的感觉,好像自己在贪污似的。
在美国开学术会,没有什么人给你送什么小黄皮信封,如果是请你去讲课,会事先讲清楚有没有报酬。如有,给你一张支票,是要扣税的。绝大部分的学术活动都没有报酬。教授的工资足够你过一个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你不会因为有500或1000块钱而去开一个会或做一个演讲,需要去的活动,没有钱甚至自己贴钱你也会去的。为什么?因为你追求的是学问,而不是钱。
高王凌:在美国,写书评是学术生涯的重要部分,不像我们这儿,你写一篇学术书评,学界、单位还不认为你这个算什么东西呢!你去报成果,这个没用,不是什么东西,还得罪人。
黄仁宇、唐德刚,“生不逢时”的那一代
时代周报:刚才说了这么多美国学术体制的好处,也得谈谈弊端。比如黄仁宇、唐德刚这两位,在国内影响较大,但在美国就处于边缘。您二位怎么看黄仁宇被纽约州立大学解聘?
王希:我们原来不知道,后来才知道的。黄仁宇先生因为他的著作出版,在美国有一些影响,但是不管怎么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相对美国史来讲仍然是一个小领域。
高王凌:美国人认为,搞美国史的才是第一流的。搞中国史的那已经是二、三流的了。过去人家主要搞的什么?在咱们之前是前苏联吧!更重要、更聚集人才。搞中国史研究最有名的还是何炳棣,当过院士。
王希:因为他的研究超出了本身的领域,这个特别重要,就是你的研究一定要超出本身的领域。
高王凌:黄仁宇也是生不逢时,先要搞“综合”在美国就不合适,这是美国的问题之一,也是优点之一,就是要先做“分析”,黄仁宇说要先做综合,再说了,他惹的那些人都是些大腕儿,都是哈佛的巨头,计量经济学界的谁谁谁。其实黄仁宇说得对,人的命运就不一样嘛,他去美国时年纪就很大了。他比余英时还大8岁,余英时给他当过论文指导教授。但是我觉得黄仁宇还是很有成就的,比唐德刚成就大,不是一个级别的。
王希:对。
高王凌:唐德刚也有很多不错的地方,但是他们还是不一样的。
王希:所以你要讲美国学术体制的弊端,可能这就是一个弊端。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它有僵化的现象。
高王凌:我说我是令狐冲,怎么怎么样,现在想,我算令狐冲又有什么呀?人家黄仁宇等于被开除了,而且是没有退休金的。那时候我跟他说,在中国替你出书吧,他说这个事儿不行啊,一定要跟台湾出版社商量好了才能做大陆版权。他的稿费都是台湾给的,了不得。太太还生着病,我见过,黄仁宇走了不到半年他太太就去世了,比他小好多岁呢。这是他的个人经历,黄仁宇就是得益于他的经历,每件事都写到他的书里了。
时代周报:唐德刚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算不算是比较明星的历史老师?
王希:据我所知,唐先生在哥大没有做过教授,他曾在哥大的东亚图书馆任职。唐先生在哥大历史系是学美国史的,我跟他认识,进哥大后,他曾跟我说“你是我之后从大陆来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他大概是1947年进的哥大,1959年博士毕业,论文写的是鸦片战争前的中美关系。
他在哥大读书和工作期间,参与了胡适口述回忆录的工作。因为国学底子很好,唐先生毕业后就到了哥大的东亚图书馆,这是北美最好的东亚图书馆之一,有非常精美的藏书,而且有很多中国的典籍。唐先生1959年拿到文凭之后没有在哥大任教,因为那个时候对华人还是相当歧视。他可能在哥大开过课,但我的印象他不是历史系的正式教授。
他在哥大东亚图书馆干了很久,升到了图书馆的副主任或副馆长,但没有做到正馆长,虽然他是完全有资格的。这就涉及到当时美国一流大学的体制问题,对有色人种还是有歧视。后来他到了纽约市立大学的市立学院,在那里开辟了亚裔美国研究,做了正教授,还做了亚裔美国人研究系的主任,在那个位置上退休。唐先生那个时候在国内名声很大,我们去他学校开会,他叫外卖,还亲自给我们端饭,我们当时都是学生,都很感动。他人特别好,一点都没有架子。
高王凌:唐德刚在口述史方面做了几件漂亮的事儿,他就是在这方面有一席之地。但在美国人心目中,这个也没有特别高的地位。比如说你做一个口述回忆录,署着你的名,但是地位不高;跟你自己写一篇,比方王希兄写一篇博士论文不可同日而语,美国是这样的。
王希:对,所以我觉得他特别可惜,如果是在现代也就是跨国史研究兴起的时代,他的学问会大放异彩的。
高王凌:那也是生不逢时。
王希:他们那一代人都是生不逢时。余英时、何炳棣是例外。
《在美国发现历史》
王希 姚平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6月版
516页,58元
本网站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及音视频),除转载外,均为时代在线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协议授权,禁止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 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转载使用,请联系本网站丁先生:news@time-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