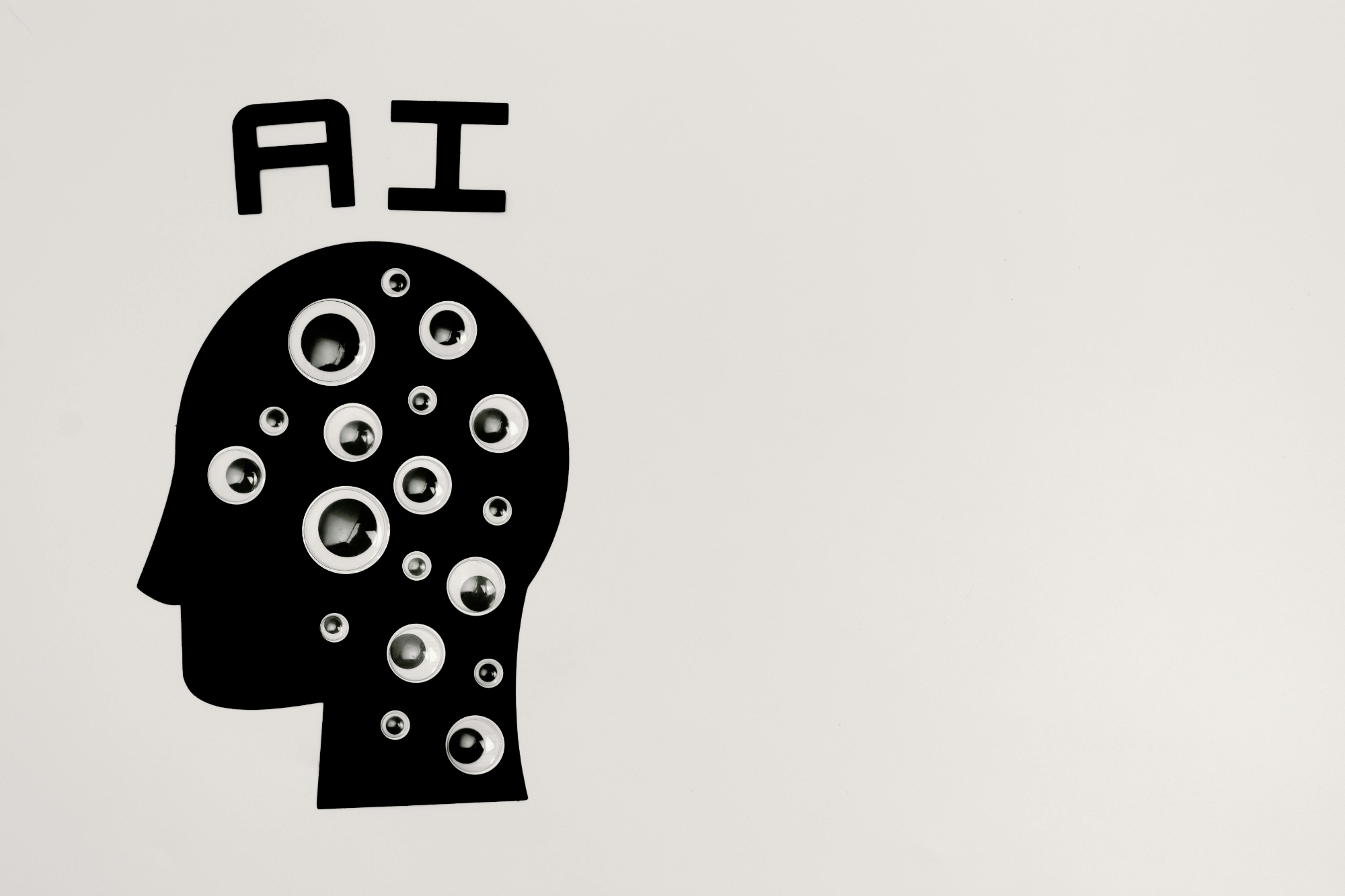鲍耀明回忆与周作人通信四五百封,屡寄生活用品
“周作人为什么给我这个无名小卒写了那么多信?不是一封二封,是四五百封。我自己时常都在想这个问题!恰恰因为我是无名小卒。如果我是出名的人,或者同周作人同辈的人,他绝对不会低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香港
香港新界元朗锦绣花园风景怡人,鲍耀明先生在妹妹鲍瑞美的照顾下,翻译、写作、会友,生活悠然自得。鲍耀明早年在商界谋生,却和许多文化人深交,更曾与晚年周作人书信交往数百封。
鲍耀明原籍广东中山,1920年在日本横滨出生,童年就读横滨的华侨小学—中华公立学校。早年的毕业生有诗人苏曼殊,和鲍耀明既是先后校友,也是同乡。中华公立学校的老师是从中国请过去的,皆热爱祖国。有天晚上,鲍耀明的同学觉得受日本人欺负,就拿石头砸破了日本人的教室玻璃。过了几日,鲍耀明和几个同学一起上街,一大帮日本学生走过来。冤家路窄,日本学生追打鲍耀明的同学们,用石头丢中鲍耀明的右眼,至今鲍耀明只能用左眼看世界。
鲍耀明读完小学,没有华侨中学可读,便开始补习日文,后考上日本中学。鲍耀明的爷爷是同盟会成员,同盟会有个俱乐部,华侨下了班,可以聊天、打麻将、下棋。日本警察对这些情形查得很清楚,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勒令鲍家限七天之内离开日本。17岁的鲍耀明随家回到离中山乡下很近的澳门。
广州沦陷后,汪精卫政府在广州成立,号召中国学生去日本留学。1939年,鲍耀明从澳门到广州应考,考中了两间日本的学校:一间是庆应大学,一间是商科大学。朋友劝他:现在中国正跟日本打仗,国立的学校就要服从国家命令,主张打仗;庆应大学是私立的,校长是自由派人士,很反战,还是去庆应大学好一点。鲍耀明进入庆应大学,一直读到日本战败。
抗战胜利后,鲍耀明回到澳门。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陈仪号召留日学生到台湾工作,鲍耀明应考到台湾省立图书馆,他非常喜欢这份工作。这时,鲍耀明的岳父开始在香港做对日贸易,他写信给鲍耀明让他回来帮忙。鲍耀明便离开台湾,回到香港,受派到东京任祥泰行经理。数年后,鲍耀明重回香港,在三井洋行任副总经理。
鲍耀明平时喜欢看书,用笔名写点杂文在报上刊登。香港的报馆请鲍耀明任驻日特派员,报道日本新闻。鲍耀明写过300篇以上介绍日本的文章,见过日本首相吉田茂,也访问过文学家谷崎润一郎等。因为报馆的关系,鲍耀明结识了曹聚仁,他回忆:“曹聚仁很特别,右派人说他左派人,左派人说他右派人,所以他在香港很不得志。因为我是做生意的,完全没有党派的观念,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所以我很怕讲政治,反倒跟曹聚仁很谈得来。”曹聚仁的生活很艰苦,时常向鲍耀明借点钱,每次借款三四百块,有时还钱,多数不还,鲍耀明也不出声。后来,鲍耀明曾笑对曹聚仁的儿子曹景行和女儿曹雷说:“你们的爸爸有很多借条在我这里呢。”
鲍耀明虽然从商,却与不少文化人志同道合,和徐吁、曹聚仁更时常相聚。鲍耀明回忆:“徐吁跟曹聚仁很有趣,曹聚仁倾向左,徐吁倾向右,常常坐在一起吵起来,但是两个人又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当曹聚仁生了大病的时候,徐吁就曾约我一块去看他。当时曹聚仁躺在床上还在写文章。”多年后,鲍耀明和徐吁喝下午茶时,曾感叹地对徐吁说:“自曹公(聚仁)过世后,留在港的五四时代人物,恐怕只有你一位了。”徐吁立即回应说:“不过,胆敢当面取笑我的人,世界虽大恐怕也只有你这荒唐先生一个!”
1950年,新加坡南洋商报社在香港中环旧东亚银行九楼设立驻港办事处,并以“创垦社”的名义,发行不支稿费的同人杂志《热风》。撰稿同人有徐吁、曹聚仁、朱省斋、李微尘、刘以鬯、高伯雨、李辉英等,皆一时之选,写外稿者则有知堂老人周作人。在《热风》同人的一次叙会中,鲍耀明向曹聚仁问起:“不知知堂老人近况如何?”曹聚仁反问:“你是否想认识他?”鲍耀明答:“我正是有这个意思。”曹聚仁说:“既然如此,我替你写信给他,不过,最好你自己也给他去封信。”从此,鲍耀明与周作人开始通信。1964年1月26日,周作人在信中提议要改称鲍耀明为“兄”,彼此渐渐无所不谈。周作人给鲍耀明的信,自1960年3月算起,到1966年5月21日止,共402封。后集成繁体字版的《周作人晚年书信》与简体字版的《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成为研究周作人晚年心境的重要史料。
交往中,鲍耀明对周作人的生活给予无微不至的帮助,不断邮寄生活物资给他,同时,周作人也把许多书画和朋友信札赠给了鲍耀明。鲍耀明对周作人深怀“同情与了解”:“从他的书信和日记,可以看到他晚年的生活与心态。其实他亦与平凡的普通人无异,他曾为患狂易的妻子而生苦恼;因经济的拮据而发牢骚;为了生计不得不忍痛出售珍藏多年的书籍与文物;为稿费的减少而亲自上门去要求改善;在处境险恶时他又不得不去求助于‘权贵’……另一方面,他博览群书,满腹经纶,在民俗、歌谣、妇女儿童问题、文学运动等领域,他写出了诸多具见卓识的好文章,更大量翻译东欧少数民族以及日本和希腊的古典名著,连鲁迅、胡适等也极口称赞他的文字,郭沫若甚至在《国难声中怀知堂》一文中说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的话。知堂老人在平凡中是否亦有不平凡之处,相信未来历史会有公允的评价的。”
鲍耀明懂日文、法文、德文、英文。日本文学的翻译不是鲍耀明的专业,却是他的兴趣。他不靠文学生活,不过有空余的时间,也喜欢集邮、古董、看旧书、翻译。2009年11月,鲍耀明开始着手翻译日本名著《东海道徒步旅行记》,2010年脱稿时,他已九十岁。鲍耀明说,翻译这本书的一个理由是,周作人曾写信告诉他,想翻译这本书,但与出版社谈不拢,于是他想完成周作人的愿望。他笑道:“因为这是我的兴趣。发表不发表是另外一回事。老人很容易老人痴呆的,有空的时候,听听音乐,看看歌剧,写写文章,我觉得这样脑筋会好点。”
五十岁时,鲍耀明写过一篇回忆录,题目为《荒唐先生的生活与意见》。如今已过四十年,他还说:“我就是荒唐,荒荒唐唐。人家说好的,我说他坏,总爱闹别扭。”
“我佩服周作人的文字”
时代周报:抗战时期,你对日本人的感情如何?
鲍耀明:我对日本人的感情很微妙。留日的学生前辈如郭沫若甚至聂耳,回到中国后多数是抗日的;英美留学生回到中国,像胡适等,多数是亲英美的,区别就在这里。我们上课时,教授在坛上讲政治问题,一说到日本天皇,日本同学都会站起来,而我们几个留学生就坐着,不站。但教授一讲到孙文,我们就站起来,日本人被吓着了。
时代周报:你在早年的时候,怎么看周作人?
鲍耀明:中学的时候,我就看过周作人的书,我佩服他的文字。他很辛苦,有家累,有鲁迅的老婆朱安,有自己母亲,有周建人的太太,又有子女。他怎么能离开苦雨斋?倘他想离开北平,如何带这帮人走?所以,郭沫若说,死一百个郭沫若都想赎周作人出来。
时代周报:抗战胜利后,胡适曾帮周作人讲话,帮他辩护。
鲍耀明:周作人曾对日本人说过一句:你们有带日本文化来吗?我觉得你们是带武化来。周作人会日本话,太太是日本人,能够保护北大的资产已经是很大功劳了。抗战胜利审查周作人的时候,蒋梦麟就说:是我叫周作人留下的。
通信几百封,“恰恰因为我是无名小卒”
时代周报:你从来没有跟周作人见过面,怎么会跟他通起信来?
鲍耀明:人家都说周作人是大汉奸。有一次,我在《热风》同人的聚会上不经意地问:“不知道周作人现在怎么样呢?”曹聚仁见过他一次,说:“他生活挺好。现在有稿费,人民政府对他还挺好。”我说:“我中学时代看过他的文章,不是很懂,但是我很佩服他,我是留日学生,他也是留日学生,所以我想知道他怎么样。”曹聚仁说:“行,我写信跟他说,同时你自己也写封信。”于是我就写了信给他。
时代周报:从书中看,你寄过很多生活用品给周作人。
鲍耀明:周作人为什么给我这个无名小卒写了那么多信?不是一封二封,是四五百封。我自己时常都在想这个问题!恰恰因为我是无名小卒。如果我是出名的人,或者“五四”时代同周作人同辈的人,他绝对不会低声下气地求你:寄点东西给我啦!就是因为我是无名小卒,他觉得无所谓。他知道我是留日学生,认识日文,所以周作人后来写的很多信都是日文夹杂在里面。只要日文更方便的时候,我就用日文写给他,周作人看得明,外人看不懂。我知道当时内地食物很缺乏,因为是三年困难时期,这里很多人寄食物、日用品给内地亲人。所以,我就跟他讲:“在我这里是举手之劳,随时有什么需要说给我听。”这样,他就开始说:“我现在想要点花生油。方便就请寄点花生油给我。”我还问他:“日本方面有很多你或许需要的书籍。我认识点人,你随时跟我说,我也可以寄书给你。”后来他想要什么,我就寄给他。
其实,我寄东西是很简单的。我当时是日本三井洋行香港分行副总经理,粮油部分也是我管的,我打个电话,让员工每个礼拜寄一次,周作人一来信我就寄给他。我对周作人讲:“不要以为我很麻烦,其实对我来说这是很简单的。”周作人还说:“我不抽烟,我的儿子周丰一抽烟。”我就寄个烟斗给他。他要什么,我就寄什么。
时代周报:当年你寄的那些东西有没有被扣过?
鲍耀明:他有时候写信来说被海关扣查过,抽税。那是人民饥荒的时候,很多东西在中途被人家拿走了,差不多有十分之一是这样收不到的—没有收到我又再寄。他对这方面似乎很感恩,也许是想“这个小子还不错啊”,便回寄东西给我。当时,他的东西拿在我手上,有朋友对我说要小心,因为大汉奸的东西,留着恐怕有问题—现在,这情形反过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很奇怪。
周作人的晚年“很辛苦”
时代周报:周作人寄了很多书画和信给你?
鲍耀明:另外他也寄了胡适之、徐志摩、钱玄同、刘半农的书信给我。甚至连属于自己的东西、沈尹默写的“苦雨斋”横幅也寄了过来。他也曾写“书生本色”的几个字给我。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寄那么多东西过来。
时代周报:周作人寄给你的这些东西后来怎么处理的?
鲍耀明:有些捐给了北京现代文学馆,有些捐给了鲁迅博物馆,有些捐给了香港中文大学,有些捐给了美国杜克大学—当然不是全部都是周作人的,有一部分是我自己的书,另外我也留下了一些周作人的东西。
时代周报:书信交往中,你觉得周作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鲍耀明:很难评论他。事实上,我不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很佩服他,他虽然犯过大错,但就是不肯离开北平。另外,周作人在文学方面的贡献,我也很佩服。
时代周报:你感觉周作人的晚年生活怎么样?
鲍耀明:很辛苦,他太太是毫无知识的。所以,我很佩服他对他的太太这么守身如玉,不会有其他问题发生。他太太晚年时常有神经衰弱病,无端发脾气,一看他的日记就知道。他的生活很辛苦,晚年写了很多文章,在香港也发表了不少。一部分是曹聚仁帮他发表的,曹聚仁之后是罗孚—当时罗孚是《新晚报》总编辑。
书信集出版“原有很多问题”
时代周报:后来你和周作人的通信是怎样结集成书的?
鲍耀明:1970年,有个上海人张莲青,在香港搞出版,我不知道他当时听到什么,跑到三井写字楼来找我。他知道周作人有信给我,说很想把这些信做成一本书发表。我当时头脑很简单,以为周作人寄给我的信拿去发表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有很多问题的,不能随便发表,会影响很多人。当时是1970年代,大陆正值“文化大革命”,湖南的钟叔河就告诉我:上面下过禁令,周作人的书不能出版。
时代周报:不少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将你们两人的通信作为研究周作人晚年的重要资料。
鲍耀明:我的目的就在这里,因为他写的信里,有很多关于“五四”时代的内容,还有他对沦陷、兄弟不和这些事情的看法—我心里也很想知道。
时代周报:那你怎么看鲁迅的文章?
鲍耀明:我佩服鲁迅,也佩服周作人,两个人作风完全不同。
实习生肖丽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网站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及音视频),除转载外,均为时代在线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协议授权,禁止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 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转载使用,请联系本网站丁先生:news@time-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