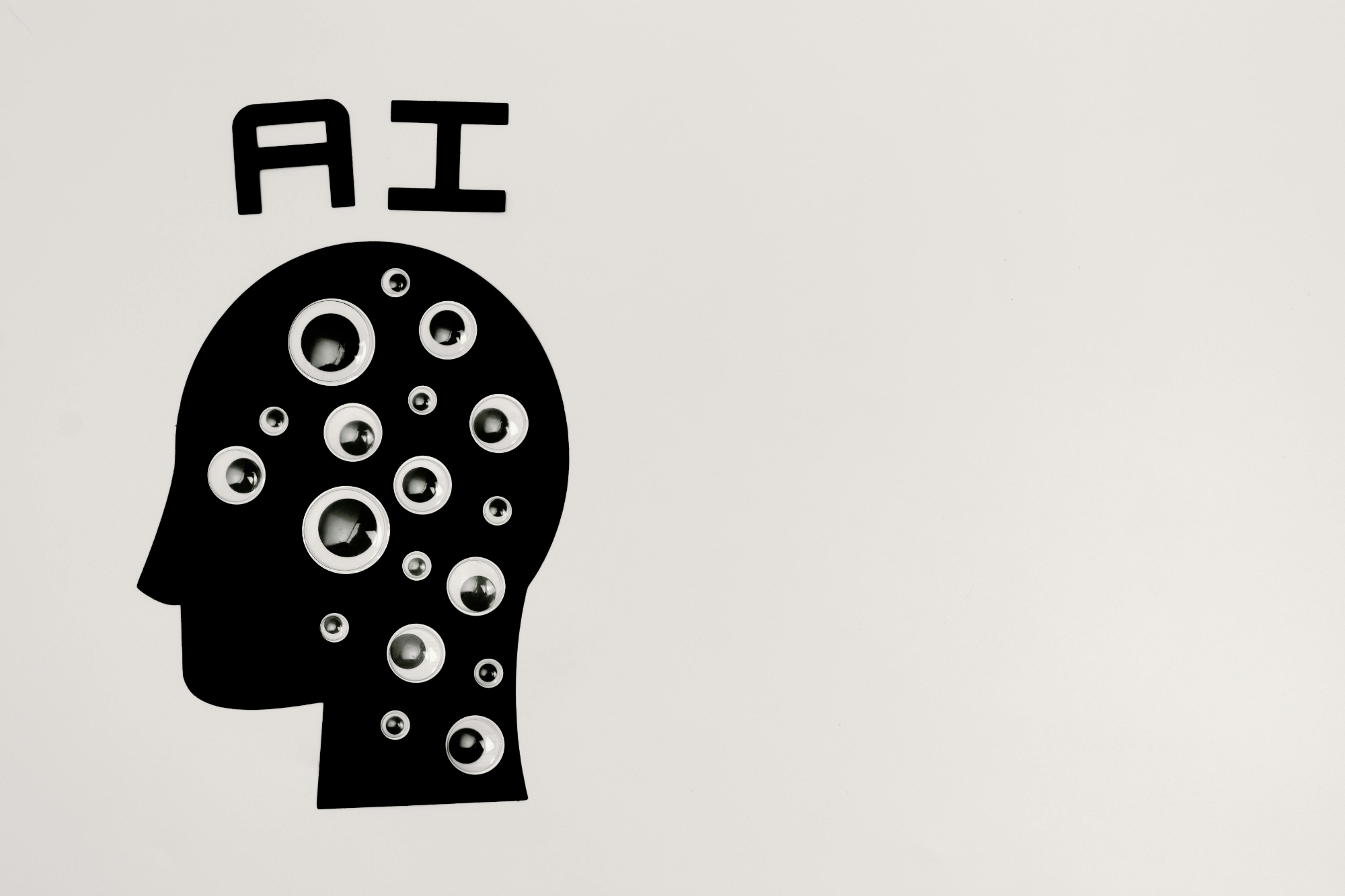普罗大众的社会担当
喻春兰
老实说,对于战争,我从来都具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感,素来对那些打打杀杀、血腥残暴的战争小说、战争电影、战争游戏、武打小说、武打电影、武打游戏都不感兴趣,对军事节目、军事武器等不愿意、也不想关心。这些东西都暗含着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生命的威胁、尊严的践踏,不管方式多么文明,武器多么先进,在本质上都是同类相残,与面对面用刀杀人、用刀砍人都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历史是一面镜子。在历史的长河中,战争史总是占有相当的分量,也是人们汲取经验教训、反思现实问题的重要素材。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待战争及其相关的书籍,对我而言,情况就不同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世界大战—二十世纪的冲突与西方的衰落》这本英文版的鸿篇巨著。作者系以研究财经史和殖民地史为长的英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和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在这本书中,他对长期以来关于这场战争的主流观点提出了挑战,并对近代史作出了富有创造性的阐释。我想,尽管作者基于文献而得出的某些观点有时会有些偏颇,他站在西方立场所作的某些表述也难以服众,但他提出的问题及其所作的回答,为人类奉献了许多精神食粮。想到这些食粮能为国人提供一些对人类的未来进行深度思考的角度和素材,我下决心把它翻译出来,与我国的读者和学者共同分享。在历时数年的艰苦的翻译、修改过程中,让我感到难以承受的,是要一遍遍地重复阅读和书写着人类所受到的巨大创伤,那发生在德国的、苏联的、中国的、前南斯拉夫的一场场大屠杀,那发生在这些国家各种各样的惨不忍睹、泯灭人性的大强奸……由此,我能深刻地感受到张纯如精神上所承受的巨大创伤。
外界一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光明战胜了黑暗、西方民主战胜了纳粹法西斯和日本帝国主义,西方取得了胜利,并以西方的胜利而结束,甚至有些人还把20世纪称作“美国的世纪”。但弗格森的结论是,这场战争,远非西方的胜利,而是全球力量平衡不可避免地向东方倾斜的历史变迁的一部分。弗格森提出并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变迁会以这么惨烈的面目出现?
在20世纪,即1900年后的100年,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时期,战争激烈的程度和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谓史无前例。可以这么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人为的、最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大战的总死亡人数中,至少有一半是平民。由纳粹及其同伙对犹大人实施的大屠杀,近600万犹太人从地球上消失了。与此同时,纳粹还杀害了大量被鉴定为“没有价值的生命”,如德国的精神病患者和同性恋者以及大量波兰的社会精英,总共约300万人。而从1938年到1953年,苏联针对少数民族或持不同政见者所造成的暴力总死亡人数达到2100万之多。
在20世纪,也就是1900年后的100年,人类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进步。由于技术的巨大进步,人类知识的增长,平均寿命延长,生活质量提高,营养水平提高,传染性疾病得到的控制,工作效率的提高,闲暇时间增多。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逃离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过着白痴式生活的农村”。福利国家已经实现了“消除物质匮乏、疾病、无知、贫穷和游手好闲”。时代的进步与战争的残暴之间是多么矛盾!
为什么在社会取得巨大进步的时候,却出现了灭绝性的种族大屠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现象?为解释20世纪人类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原因,弗格森通过对20世纪世界各主要国家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描述和分析概括出了以下原因: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而导致的种族冲突、社会经济发展的突然中断、古老帝国的衰落和新兴帝国的兴起。
谁是最后的赢家?在弗格森看来,20世纪最大的事件就是西方对亚洲统治的削弱,是西方的衰落,东方的崛起。
弗格森虽然讲的是世界历史,但他提出的问题,却非常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稍远一点的,是我国50多年前的那场大饥荒。从1959年到1961年即“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民经济空前萧条、低迷。全国工厂关停近半,2000多万新招职工被驱回农村。因粮食的短缺,广大乡村爆发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还有接下来的,是把全国人民抛入苦难深渊的长达10年“文化大革命”……近一点的,是近年来多起毒害婴儿、校园枪击、杀亲、社会腐败等各种匪夷所思、令人痛心的社会现象。
为什么社会越是进步,人类却越是反常?这个世界究竟怎么啦?人们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找出主谋—真正的肇事者,而且会把所有的责任推卸给某一个人,如希特勒、斯大林等等,而且在宏大的叙事中,人们只需这么一推,便落得个干干净净、白壁无瑕。更何况,无论是肇事者还是参与者,都会得到受害者或者旁观者的同情和谅解。有自我反省能力或者愿意进行反省者少之又少,非常难得。自作孽,固然不可活,但当人们把所有的愤怒和谴责都投向某个人的恶行时,是不是也应该想一想,在社会倒退的过程中,普罗大众—相对于强势集团的那些弱势群体,尤其是代表良知的知识分子难道就没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吗?在希特勒这样的个体作孽之时,德国的大多数,都在做什么?或者说做了什么?难道他们不应该在种种血腥的大屠杀面前解剖自己、做出深刻的反思吗?难道他们不应该在千万个恶行的牺牲品面前摸着自己的良心忏悔自己自觉不自觉、有意或无意的参与、沉默、容忍或纵容吗?易卜生有一句名言:“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的确如此。这句话也让我想起来了美国著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来。
汉娜·阿伦特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被公认为是极权主义系统研究的开山之作,它与1941年弗罗姆的《逃避自由》、1944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等著作一样,是那一代饱受战乱之苦的知识分子对极权主义和乌托邦思想的反思成果。该书主要分析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类政治大灾难—极权主义,包括德国的纳粹主义和苏联斯大林的大肃反。阿伦特在《纽约客》杂志发表了系列报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篇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提出了“平庸的恶”这一概念,从而把普罗大众这一群体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她在报道以色列对纳粹分子艾希曼的审判时,发现这个罪大恶极的人并不是某种彻底邪恶的化身:艾希曼就是这样一个“好人”,他服从命令、尽职尽责,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陈词滥调他根本不会开口”。他只是一个无法判断、无法反思的平庸的官僚。在她看来,艾希曼完全不像一个想象中的恶魔,一个没有心肝的人。她望着站在玻璃盒子里的艾希曼,觉得他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小丑”。是缺乏了个人的判断,才导致他可以轻易地规避整个道德体系。这使得阿伦特不禁自问:为什么像纳粹这样的政权,恰恰是靠艾希曼这样的既肤浅又平庸的“好人”来支撑、来维持的呢?于是她想到了“平庸的恶”这个词。她说:“恶一向都是激进的,但从来不是极端的,它没有深度,也没有魔力,它可能毁灭整个世界,恰恰就因为它的平庸。”在她看来,是极权主义抹杀了所有的公共生活,抹杀了所有的自我。极权主义就像某个一旦开动后就不肯停止的搅拌机,所有东西都被搅成一团。在极权主义之下的个人,成为某种封闭的东西,某种暂停运转的东西。他们只能被动接受现成的东西,就像一个只能接受输液的植物人。
为了历史悲剧不再重演,阿伦特认为重要的是要建立在个性自我基础上的公共生活,要让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学会交流和判断。在判断之下,任何绝对真理,都只能以某种意见的身份出现;种种恶行,因而也就无法再以正义或真理之名大行其道。
在社会进步中的种种历史倒退现象面前,对于普罗大众而言,确实需要罕见的勇气、真正的思考和正确的判断,才能不被卷入这种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平庸大众及其不加思考的恶行潮流之中,保持自身的清纯与高洁、清醒与警醒,才能在面对平庸的恶时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担当而不是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之中;对于社会、对于国家而言,只有把现代国家建立在真正的民主而不是“金喇叭”式的民主基础之上,大力拓展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空间,赋予每个公民、每个平凡的人以社会责任,让人们在交流中学会判断,学会过公共生活,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本网站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及音视频),除转载外,均为时代在线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协议授权,禁止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 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转载使用,请联系本网站丁先生:news@time-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