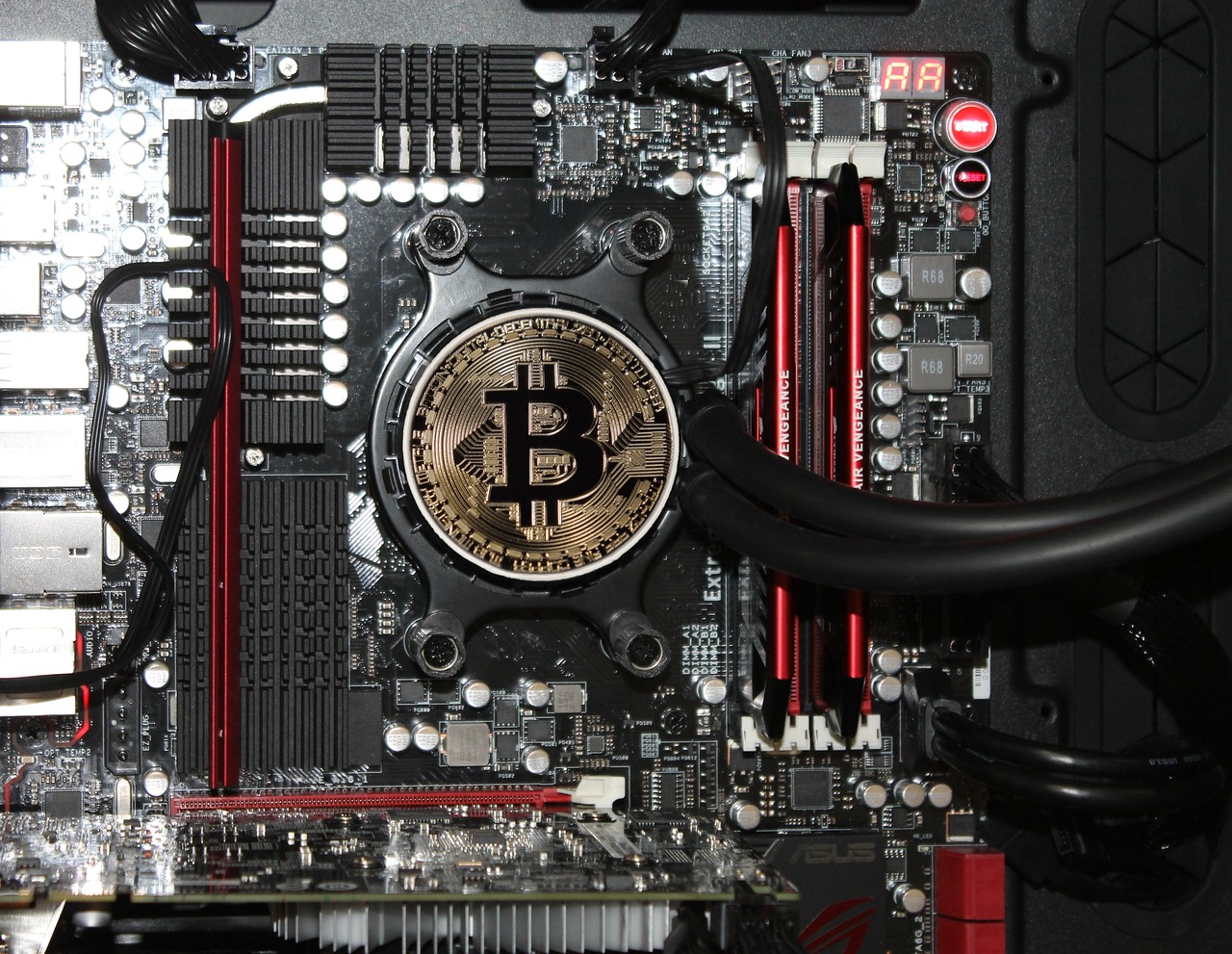中国学人的哈佛情缘
李欧梵的《我的哈佛岁月》和黄进兴的《哈佛琐记》讲述的哈佛大学故事相映成趣。李欧梵和黄进兴都师从史华慈,皆受余英时教益,先后在哈佛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后来都成了台湾“中央研
本报记者 李怀宇
李欧梵的《我的哈佛岁月》和黄进兴的《哈佛琐记》讲述的哈佛大学故事相映成趣。李欧梵和黄进兴都师从史华慈,皆受余英时教益,先后在哈佛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后来都成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欧梵在哈佛的“国际路线”
(李欧梵 林津鹭 摄)
1961年,李欧梵在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在即,感到前途茫茫,于是随着班上大部分的同学申请赴美。他到处乱寄申请信,后来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都准备收他,芝加哥给他免学费的待遇,哈佛则给他“另类奖学金”,是“备取”或“候补”的意思:如果别人不要那份奖学金,他或有机会,否则无望。李欧梵不想再增加父母的经济负担,决定就读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专业。
后来,李欧梵还是决定申请到哈佛大学研究中国问题。当他遍查哈佛的课程表,没有中国现代文学的科目,而中国历史方面,除了费正清教授外,只有两个不甚熟悉的名字:L. S. Yang(杨联)和Benjamin Schwartz(史华慈)。芝大一年快结业时,他收到哈佛的入学许可,而且有全部研究院的奖学金,在1963年暑假从芝加哥搭顺风车到了波士顿。
初入哈佛,李欧梵就立下三大志愿:除了多旁听课之外,就是故意少与我族类来往,甚至为自己的社交生活开创一个新局面—“泡洋妞”。因此他不久就以专走“国际路线”驰名。
当年在哈佛政府系最有名的教授是基辛格。李欧梵去旁听他的一门大班课—“国际关系理论”,第一堂他未开讲前早已挤满了学生,教室是音乐系的演奏厅,基辛格坐在演奏台上,任由四五位助教在台前讲述本课的要求和指定作业,足足说了20分钟。然后,基辛格才从太师椅上站起来开讲,不慌不忙,一口作秀式的德国口音。在李欧梵的眼中,不免觉得基辛格简直就是一位政客。据说基辛格在尼克松手下当完官后想返回哈佛重执教鞭,却被哈佛政府系的全体教授拒绝。
哈佛最开心的事是泡图书馆,李欧梵常在怀德纳图书馆的层层藏书架前流连忘返。他回忆:“看累了则偷看别人,一饱窥视欲,特别是看到漂亮的女生,则更可做‘眼睛捉迷藏’的游戏。在怀德纳图书馆看书的以研究生为主,所以要找靓女,还需要移师到本科生的图书馆。我的惯例是:如果一天没有课,则早上到怀德纳图书馆,下午到本科生的拉蒙(Lamont)图书馆,晚上有兴致时则去距离较远的蕾克列芙女校的图书馆,当然醉翁之意不完全在酒,偶尔也会有“艳遇”。在拉蒙图书馆看书有另一个好处:它的阅览室有落地玻璃长窗,窗外风光一览无遗。我往往在此看书至五六点钟晚餐时刻,看到窗外的一群群一年级学生到附近的餐厅去吃饭,一副得意的样子,令我既羡慕又忌妒,因为哈佛的本科生才是天之骄子,每个人都是雄心勃勃。当时流行着一则笑话:如果一群本科生去餐厅时被汽车撞倒了,这会成为一件大事,因为其中就可能有将来的总统和议员。而我们这些研究生则是可有可无,在一年级学生的眼中,我们都是大学花钱养的废物。有时候我看到这一群哈佛园新来的年轻人,天真烂漫地嬉戏于夕阳斜照的拉蒙图书馆窗前,也不免感到老大徒伤悲,其实我那时候还不到30岁。”
在哈佛大学念中国近代史,李欧梵的主要目的是跟随费正清教授。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兴趣更接近思想史,所以后来拜史华慈教授为师。入学后的第三年,他和费正清的关系开始接近起来。费正清公开称李欧梵是一个“放荡不羁者”(free spirit),请李欧梵参加他家的茶会。李欧梵因此认得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还不止一次和少数研究生应邀在周末到费正清的避暑山庄去小住。几个学生初抵山庄不久,费正清就带着他们去砍柴,体力劳动数小时,有一次,费正清还率先跳进一个泥泞的小池塘中,要同学们先洗一个“自然澡”。晚餐后闲谈一阵,费正清就早早就寝了。第二天费正清一早起身,立刻到他的小书房去工作,整天除三餐外足不出户,据说是数十年如一日。李欧梵了解到,费正清在周末以外的工作日生活更是严谨:每天清早起身,上午四个小时绝不上课或见人,而是独自躲到他在怀德纳总图书馆的书房中去看书,每天下午才去上课、上班和处理公务。后来费正清对李欧梵说:“以后你们教书忙起来,每天能抽出两三个小时读书就够了!”
叛逆性格
李欧梵的论文尚未完成时,要求先到欧洲去“游学”半年,并找寻写论文的“灵感”。费正清欣然答应,还为他弄到2000美元的奖学金去欧洲各国游历。李欧梵成行前向费正清致谢,费正清给了他三封信,要他在适当时机交给费的三位欧洲汉学界的朋友。其中一位是当年在伦敦执教的Stuart Schram教授,当李欧梵把费正清的信拿给他,他看后大笑说:“看来费教授要我带你到酒吧去喝酒,他说你是一个free spirit!”
史华慈曾是费正清的及门弟子,但费正清曾公开承认学问特别是在思想史方面不如他。史华慈年少时在波士顿上“拉丁中学”就开始会拉丁文,在哈佛读本科生时专修的是法国哲学,二战服役时又学了中文和日文,德文和希伯来文则有犹太人的家学渊源。除了法文外,他又兼及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据说,有一次史华慈到意大利开会,早晨打开报纸看后大谈中国新闻,别人都目瞪口呆,原来该地没有英文报纸,他看的是意大利文报纸。有一次李欧梵到史华慈家拜访,亲眼见到他和夫人吵架,原来吵的原因是他到底懂得几种语言,他夫人说他至少懂十国语言,他坚持只懂六七种。
李欧梵最后一次去看史华慈,史华慈已因癌症复发而卧病在床,医生早已束手无策,事实上他在等死,但却十分宁静。李欧梵回忆:“他像慈父一样向我和玉莹(当时我们尚未结婚)问候生活情况,目光慈祥。我顿时感动起来,向他报告说:想提早退休,如此可以多一点时间过一种‘静思型生活’。我当时不自觉地用了他批评阿伦特的那篇文章中的两个字眼,竟然把‘静思生活’的拉丁文说成‘vita contemplate’。他听后不置可否,但立即纠正了我的语言错误:‘不是contemplata,是contemplativa!当年我是念过拉丁文的。’”
英国思想家伯林的名著《刺猬与狐狸》,灵感源于古希腊诗人阿尔基诺库斯的残句:“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以此论之,李欧梵是“狐狸”,同属史华慈门下的张灏则是“刺猬”。李欧梵回忆,当年在哈佛大学向史华慈学习中国思想史时,老师对他特别开恩,让他做什么都可以,于是他很自然地把思想史和文学史混在一起学习。“史华慈的教法是古今不分的,他写毛泽东,后来又写中国古代,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当年美国的汉学界是看不起现代文学的,我要争这口气,就想办法阐释现代文学,这是我的叛逆性格。”
在哈佛大学当研究生,最担心的是博士口试和论文答辩。博士口试时,李欧梵开始表现不错,到了最后考中国现代史,费正清说:“你刚才回答俄国史问题的时候,好像对于历史上的日期不大清楚。那么我也问几个日期的问题:国民党的前身中华革命党哪一年成立?”“1913年。”李欧梵立刻回答,心中早已开始慌乱了。接下来,费正清连续问了李欧梵十来个日期,使李欧梵惊慌失措。费正清以主考官的身份对李欧梵说:“回去吧,明天我让秘书通知你结果。”
那一晚,李欧梵失眠了。第二天傍晚时分,费正清的秘书告诉李欧梵口试通过了。不久,李欧梵接到费正清亲自打电话来安慰:“我们男人考博士口试,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样,孩子生前有阵痛,痛完了生下来就好了!你就把它当作一时的阵痛算了,没有关系。”
黄进兴梦寐以求的快乐时光
(黄进兴 本报记者 李怀宇 摄)
1976年,黄进兴从台湾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后赴美留学,第一站到了匹兹堡大学。此后由余英时先生推荐,黄进兴转读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的6年读书生涯,是黄进兴梦寐以求的快乐时光。以前在台湾大学读书时,黄进兴无法早起,常常12点才去课堂,而到了哈佛大学,早上五六点就起床,醒来就要读书。有位朋友到他的宿舍,看见书堆到天花板,说:“幸好波士顿没有地震,不然你的书倒下来,会把你压死。”
在哈佛大学,黄进兴常常去旁听一些大师级教授的课,印象颇深的是《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有一次,一位朋友远道而来哈佛,他心仪罗尔斯已久,意欲随黄进兴去旁听。波士顿初秋的下午,夕阳斜照,有点暖意,最适合听哲学讲演。罗尔斯那天很卖力地论述他对康德哲学的解释,意在反驳20世纪“功利主义”的大师穆尔的论点。黄进兴回忆:“罗尔斯讲到紧要处,适巧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照在他身上,顿时万丈光芒,衬托出一幅圣者图像,十分眩目。正想提醒我的朋友把握住这段历史的片刻,作为哲学的见证,没料到他老兄竟然东倒西歪地呼呼入睡。”
学期结束,罗尔斯讲完最后一堂课,谦称:课堂所谈全属个人偏见,希望大家能做独立思考。全部学生立即鼓掌,向他致谢。罗尔斯频频挥手,快步走出讲堂。在他走出后许久,掌声依然不衰,黄进兴的双手拍得又红又痛,问了旁边的美国同学到底还要拍多久,他答道:“让罗尔斯教授在遥远的地方还可以听到为止。”
那时的哈佛大学可谓大师云集,黄进兴受史华慈和余英时两位史学大家教益良多。黄进兴刚到哈佛大学那一年,余英时先生即受耶鲁大学礼聘为讲座教授。余先生偶过波士顿时,有一晚电话召黄进兴聚谈,深夜和余先生步行到唐人街吃夜宵,黄进兴听余先生一再说:“做学问说穿了就是‘敬业’两字。”从古人的“闻道”到余先生的“敬业”,黄进兴灵光一闪,似乎看到近代学术的真精神。
黄进兴第一次走进史华慈的研究室,门敞开着,但是外头坐满一排人,个个做沉思苦闷状。室内史华慈谈笑风生,造访者更是手舞足蹈。黄进兴仿佛置身于医院的候诊室,而史华慈极像名医,各科知识上的疑难杂症,一经诊断,药到病除。由于候诊者众,好不容易才轮到黄进兴,虽然只有短短的5分钟,他发现史华慈是位很谨慎的医生,在症状不明之前,不随便开药方。
在会谈中,有位学生闯进来要跟史华慈拿介绍函,史华慈极亲切地和他打招呼,连说:“准备好了,只差你的名字没有填进去,请问你的尊姓大名?”黄进兴和这位学生一起走出来,听他抱怨说,他已经跟史华慈念了五年书,至今史华慈仍然记不起他的名字。据他说,比起另一位同学他还算幸运。那位学生刚从越战回来复学,跑去找史华慈教授讨论问题,相谈甚欢,史华慈教授很兴奋地告诉他:“我以前有一个学生的思想和你十分接近。他叫某某某。”其实眼前的那位学生就是史华慈记忆中的某某某。
“我希望我能同意您,但是……”
史华慈因个人稳健厚重的学风,门生满天下。而有些社会科学家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理论模型,往往经不起史华慈锐利的批评,因此有人戏称他为“理论的破坏者”。因为他的讲话常常带有口头禅:“我希望我能同意您,但是……”于是学界封之为“但是先生”。
在生活上,史华慈不断帮黄进兴申请奖学金。他很怕外国人在美国饿死,有一次问黄进兴:“你有食物吗?”黄进兴听了很不好意思,说:“有啦。”哈佛前两年是保证有奖学金,以后每年都要重新审核。有一次黄进兴经过系办公室,一个助教跟他说:“你有奖学金,老师很关心你,帮你申请。”
黄进兴认为:“史华慈先生很有人文素养,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在二战是上尉,搞情报破解的,是破解日本无条件投降密码的重要人物。他对犹太文化的认同感很强,他儿子还回以色列当伞兵。他对各方面文化的认同都很强,所以也可以了解中国人的心情。他对中国文化抱着同情和理解,不像某些洋学者主观认定西方文化优越感。他培养了不少中国的学者,林毓生先生、张灏先生、李欧梵先生等前辈学者,都是他的学生。”
有一次史华慈跟黄进兴聊天:“你有这样的底子,做西方的学术当然很好,但是在西方有很多可以做得更好的人,你不算突出。为什么不回去做中国学问?一般做中国学问的人没有你这样的底子,你有不同的眼光和训练,说不定会看出一些有趣的问题。”史华慈并不知道黄进兴事先就认识了余英时,说:“你要在中国学方面打点基础,我介绍你到耶鲁去跟余英时教授好了。”随后史华慈打电话给余英时。黄时兴每隔两三个月就去余英时家住一两晚。每一次都聊到晚上三四点。因为聊得太晚,就干脆在余英时家睡,醒来再聊一下,下午才走。他回忆:“余先生在耶鲁,是最多产的阶段,很多好作品出来。他每次有文章总会让我们看,我们算是最初的读者。有时我们就提供一些意见,我是主要批评者,鸡蛋里挑骨头。我那时等于读了两个学校,耶鲁和哈佛,常常来来去去。”
在哈佛大学,黄进兴打下了比较全面、扎实的学问底子。他的博士论文题目《18世纪中国的哲学、考据学和政治:李绂和清代陆王学派》实际上是余英时给的,后来幸运地被剑桥大学出版社接受出版。他说:“李绂是清代陆王学派最重要的人,但没有人做,很隐讳,是一个次要的思想家,因为是次要的,反而更能反映一个大时代的气候。因为第一流的思想家、学者往往超越那个时代,走在前面,要谈朱熹、王阳明反映了当时什么,很难。但李绂更能反映当时学术的气氛。”
黄进兴在哈佛拿到博士学位后,特向史华慈辞行,史华慈临别赠言:你在求学期间,花了不少时间修习、研读西方课程,可是在博士论文里,竟不见踪影。希望有朝一日,能将东、西方的知识融会贯通,好好发挥。黄进兴觉得老师的针砭,宛如佛家醍醐灌顶。
从美国学成回到台湾后,黄进兴以太太的名字“吴咏慧”写了一批回忆哈佛大学生活的文章,后来集成《哈佛琐记》一书。不少人常常误以为《哈佛琐记》的作者是一位女作家。有一次,李欧梵和黄进兴在新竹清华大学见面,问道:“台湾有一位女作家叫吴咏慧,文章写得很好,你认识她吗?”黄进兴说:“不认识。”
本网站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及音视频),除转载外,均为时代在线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协议授权,禁止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 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转载使用,请联系本网站丁先生:news@time-weekly.com